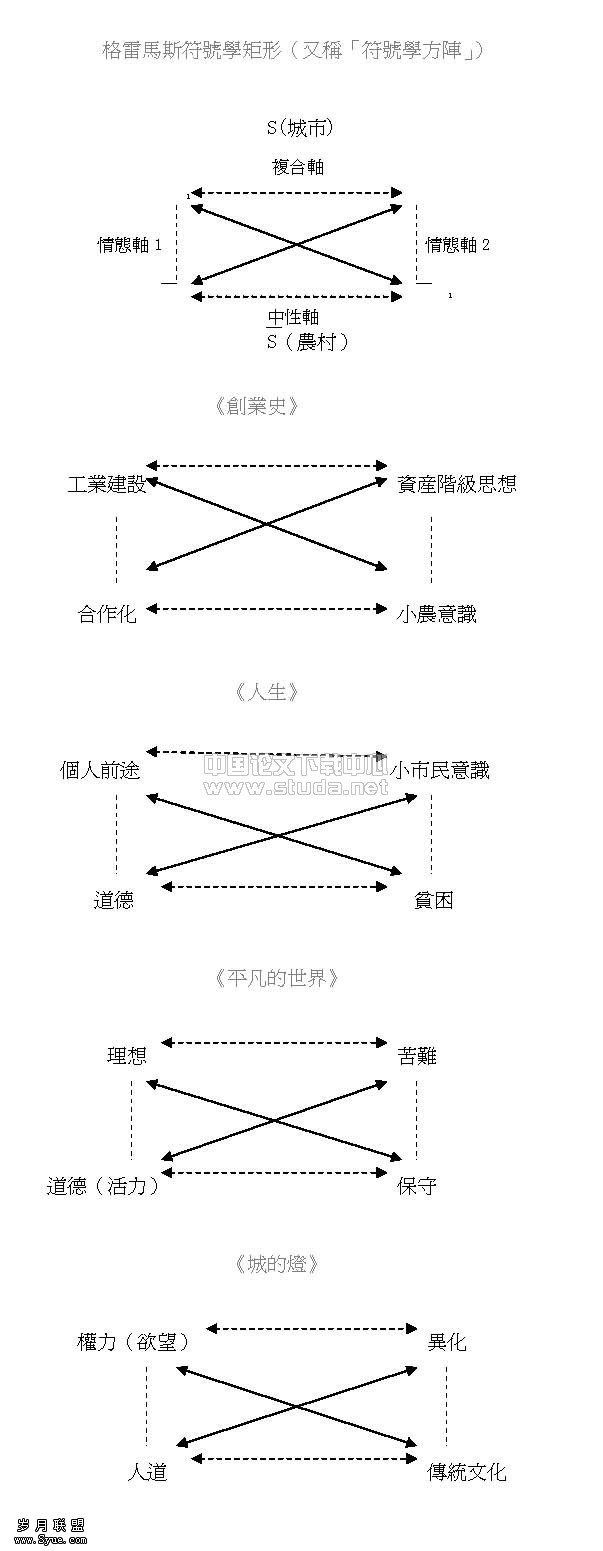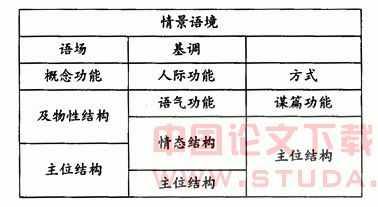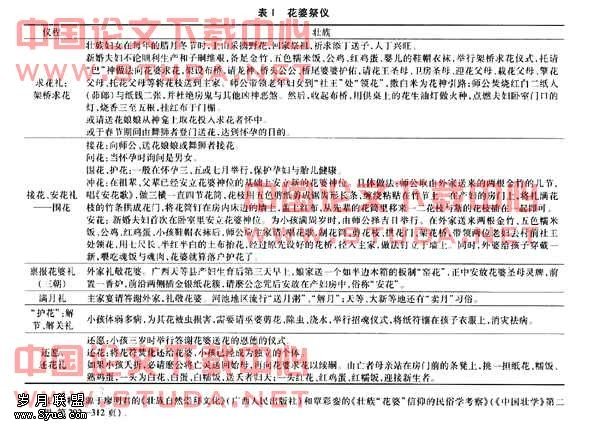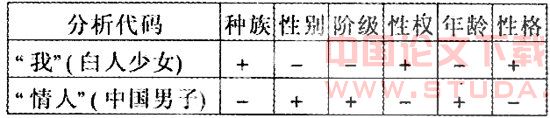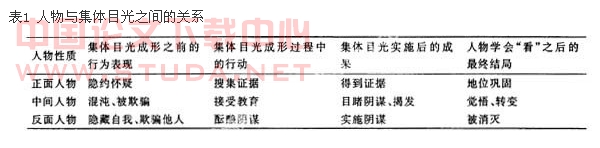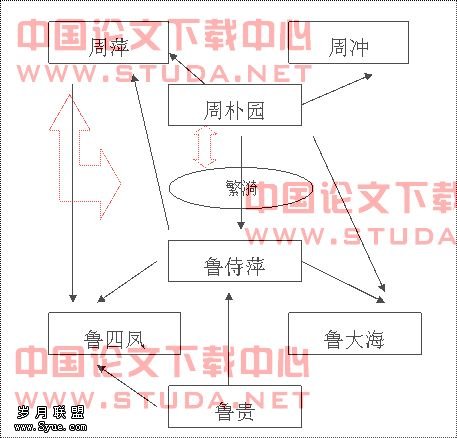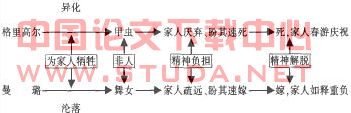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下)
学术之兴趣,而力求进步。1;Ⅴ
“学术讲演会”的具体地点,在部会场、北京高师和北大法科礼堂。原先刊出的广告,第一讲是章士钊的“论”,后因章临时外出,改为陈大齐的“心理学”1;Ⅵ。在此后的三个月里,除了上述二题,还举办过如下题目的系列讲演:社会与教育(陶履恭)、燃料(王星拱)、墨翟(胡适)、天文学(高鲁)、放射性化学(俞同奎)、教育学(邓萃英)、生物与人生哲学(李煜瀛)、社会与伦理(康宝忠)、相对论(何智杰)、学(陈启修)、园艺与害虫学(夏树人)等。如此规模的“学术讲演”,在让大学走向社会的同时,也让“演说”承担起传播高等学问的责任。
教授们不再只是针对社会问题发言,而是努力向公众传播自己所擅长的专门知识。这么一来,如何有效地演说“学问”,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受到学界以及社会的共同关注。当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口说”,将“讲坛”搬到了纸上,所谓的“著述”风格,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嬗变。如果采用的是传统的讲学形式,以解读经典为中心(如《复性书院讲录》)1;Ⅶ;或因职责所在,演说时学术性不是很强(如《蔡孑民先生言行录》)1;Ⅷ,那么,将其言谈记录下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但若讲授的是专深的学问,要实现从“声音”到“文字”的转化,难度就大多了。
这就牵涉到晚清的另一个新生事物——速记法。梁启
超特别推崇的日本政治小说《经国美谈》,止是久野龙溪采用口述笔记的形式完成的;“同时他在卷尾附录了一篇名为《论速记法》的文章,向《经国美谈》的读者介绍了‘速记法'”1;Ⅸ。对于《清议报》能及时地译介“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的《经国美谈》,梁启超十分得意,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特别予以表彰1;Ⅹ。一年后,梁撰《新未来记》发表,第一回中有如下一段:
却说自从那日起,孔老先生登坛开讲,便有史学会干事员派定速记生从旁执笔,将这《中国近六十年史讲义》,从头至尾录出,一字不遗。一面速记,一面逐字打电报交与横滨新小说社登刊。1<Ⅰ
如此强调“速记”,明显受《经国美谈》的启发。所谓“一字不遗”,当然过于夸张;但速记的出现,使得“演说”之成为“著述”,平添了许多可能性。
谈论中文速记,一般从蔡锡勇说起。京师同文馆毕业后,蔡在驻美使馆任参赞期间,对当时美国流行的“快字”感兴趣;回国后,美国凌士礼(Lindsley)的速记法,撰成《传音快字》一书,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武昌刊行。到了清廷推行新政,设置咨政院,开会时亟需速记员,于是召蔡的儿子蔡璋进京,创办速记学堂,并将其父的《传音快字》改编为《中国速记学》,于1913年正式出版1<Ⅱ。此后,不同的速记法纷纷面世,对学术文化的整理以及思想的传播,发挥了很大作用。
然而,在这中间,陷阱依然很多——即便速记员训练有素,还有口音差异,以及话题的专业性等。一般的社会动员或知识普及比较好记,倘若是“学术讲演”,可就没那么轻松了。章太炎晚年曾拒绝刊行未经自己审定的讲演稿1<Ⅲ,就是担心记录有误,以讹传讹。此举并非多余,谓予不信,请看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经历。《新青年》3卷1号的“通信”栏里,收有蔡元培致《新青年》记者函:
《新青年》记者足下:鄙人归国以来,偶在会场演说,事前既无暇预备,事后亦不暇取速记稿而订正之。日报所揭,时有讹舛,以其报仅资一阅,即亦无烦更正。不意近日在政学会及信教自由(会)之演说,乃为贵杂志所转载,势必稍稍引起读者之注意。其中大违鄙人本意之点,不能不有所辨正。1<Ⅳ
蔡元培自称信奉引力说及进化论,可报载他在信教自由会的讲稿,竟阑入一大段“宗教家反对进化论者之言”,让他实在不能容忍。至于“政教会演说报纸所载有漏脱,有舛误,尚无增加之语”。其中“最为舛误者”,蔡开列了十条,逐一辨正。
此信让既是北大文长、又是《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狼狈之至,赶紧以“记者”名义附言:“本志前卷五号,转录日报所载先生演说,未能亲叩疑义,至多讹误,死罪死罪。今幸先生赐函辨正,读之且愧且喜。记者前论,以不贵苟同之故,对于先生左袒宗教之言,颇怀异议。今诵赐书,遂尔冰释。”1<Ⅴ引领学界风骚的《新青年》尚且如此,其他报章的情况可想而知。
正是有感于此,后人为慎重起见,不太敢用报刊上的演说资料。可完全放弃这些口述实录,又实在可惜。若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其《凡例》的第一则称:“本书所收以先生亲自撰著之文字为限,其为先生口述,他人笔录或代作者,如先生生前各报刊登之谈话、语录、讲词等,一概不收。”1<Ⅵ严守边界,宁缺毋滥,固然是好事;但对于研究者来说,我还是更喜欢半个世纪后朱维铮所编篇幅剧增的《马相伯集》1<Ⅶ。
不再满足于固守书斋的现代中国学者,开始走出校园,面对公众,就自己熟悉的专业发表公开演讲,而且借用速记、录音或追忆等手段,将“口说”变成了“著述”。对于此类不够严谨专深、但也自有妙用的“大家小书”,到底该如何评价?
倘若速记者听得懂方言,有较高的文字修养,也能大致理解演讲的内容,这种情况下,速记稿还是可信的。当然,正式出版前,需要演讲者做一番仔细的修订。1922年商务印书馆初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封面署的是“梁漱溟讲演,陈政、罗常培编录”。为什么这么署,不外是突出速记者的成就与责任。在《自序》中,梁漱溟称:“这是我今年八月在山东济南省教育会会场的讲演,经罗君莘田替我纪录出来,又参酌去年在北京大学讲时陈君仲瑜的纪录而成的”;“在别人总以为我是好谈学问,总以为我是在这里著书立说,其实在我并不好谈学问,并没在这里著书立说,我只是说我想说的话。”1<Ⅷ更有意思的是,这部现代学术史、思想史上的名著,连序言的落款都是“中华民国十年十月二十二日漱冥口说陈政记”。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一代名著。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就曾给予此书高度评价:“在当时大家热烈批评中西文化的大潮流中,比较有系统,有独到的见解,自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东方文化说话的,要推梁漱溟先生在一九二一年所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1<Ⅸ
以“演说”为“著述”,不是完全不可行,除了演说前的殚精竭虑以及演说中的超常发挥,还依赖以下三点:一是需要好的记录稿,二是需要作者认真修订,三是需要读者转换阅读眼光。对此,举三本书,略作说明。
1932年,周作人应沈兼士的邀请,到辅仁大学作系列演讲。因其平日所思所感,别有会心,“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看过邓恭三(即日后成为著名学家的邓广铭)的记录稿后,周大为称奇:“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于是,将讲稿交北平人文书店刊行。表面上,作者姿态很低,一再谦称此书“只是临时随便说的闲话,意见的谬误不必说了,就是叙述上不完不备草率笼统的地方也到处皆是,当作谈天的资料对朋友们谈谈也还不妨,若是算它是学术那样去办,那实是不敢当的”。可接下来的
这句话,可见作者并非真的那么谦卑:“我的意见并非依据西洋某人的论文,或是遵照东洋某人的书本。”单是“这讲演里的主意大抵是我杜撰的”1<Ⅹ,便可知作者的立意与抱负。在众多关于此书的评论中,钱钟书的意见最值得重视。钱对周说有所批评,但还是承认:“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正如一切的好书一样,它不仅给读者以有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1=Ⅰ。称周书“有系统”,实在有点勉强;但要说引起“许多反想”,那倒是真的——时至今日,此书还在被人阅读、批评、引证。
1961年,应香港某学术机构的邀请,钱穆就“历史研究法”这一总题作了八次演讲。作者称:“这次一连八讲,由于时间所限,所讲总嫌空泛肤浅,又是语焉不详。我不能站在纯历史纯学术的立场来讲话,有时不免带有情感,随便空说,请诸位原谅。”1=Ⅱ此讲演集,先由叶龙记录讲辞,再经钱穆本人整理润饰,1961年刊行于香港,1969年在台北重版。到了为台北版作序,钱穆开始自得起来,提醒“读者勿忘我此八番讲演之主要意义所在”。所谓“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明显有所指。在钱穆看来,主流学者只讲研究方法,不考虑历史背后的文化与意义,并非理想的学术境界1=Ⅲ。同样是在香港,同样是为非本专业的学生讲课,牟宗三讲的是中国哲学。牟说得没错,在总共十二小时的系列演讲中,“想把中国哲学的特质介绍给社会上公余之暇的好学之士,当然是不很容易的”。可成书时,作者显然颇为得意,其《小序》相当有趣,值得大段引录:
本讲演并无底稿。在讲述时,托王煜同学笔录。口讲与自己撰文不同,而笔录与讲述之间亦不能说无距离。如果我自己正式撰文,也许比较严整而详尽。但有这个时间限制的机会,也可以逼迫我作一个疏略而扼要的陈述。这也自有其好处。而王君的记录也自有其笔致。换一枝笔来表达,也自有其新鲜处。顺其笔致而加以修改,也觉得与我的原意并不太差。紧严有紧严的好处,疏朗也有疏朗的好处。是在读者藉此深造而自得之。1=Ⅳ
好一个“疏朗也有疏朗的好处”,一下子点到问题的关键,也说透了学术演讲之所以吸引人的奥妙。至于“顺其笔致而加以修改”,更是道尽此类文章或著述的特点。
周、钱、牟三书,都是“小而可贵”。惟其篇幅小,讲者(作者)不能不有所舍弃;也正因此,面貌更加清晰,锋芒也更加突出。所谓“虽非著述之体,然亦使读者诵其辞,如相与謦于一堂之上”1=Ⅴ;不以严谨著称,但“疏略而扼要”,“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在一个专业化成为主流、著述越来越谨严的时代,此类精神抖擞、随意挥洒、有理想、有趣味的“大家小书”,值得人们永远怀念1=Ⅵ。
比起“文字的中国”来,“声音的中国”更容易被忽略。引入随风飘逝的“演说”,不仅是为了关注晚清以降卓有成效的“口语启蒙”,更希望借此深入了解近现代中国的文章风气以及学术表达。附记本文初稿于2005年4月28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的“东京大学2005AT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亚洲视野中的中国学”上宣读;二稿于2006年1月20日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召开的“东亚近代言语秩序的形成与再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三稿提交给东京大学主办的“近代东亚的知识生产与演变”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7月21日)。与会者的评议及提问,使我的思考得以不断深入,特此致谢。2006年8月16日,定稿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注释:
①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4卷11—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②周谷城在《“五四”时期的自由辩论》一文中,简要评说五四时期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等四个方面的“自由辩论”,结尾是:“‘自由辩论',即在近日的学术界,仍值得提倡,故特举出于此”。参见《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411—4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③1<Ⅰ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一回,《新小说》1号,1902年11月。
④李伯元:《文明小史》,1903—1905年连载于《绣像小说》,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吴蒙《学究新谈》,1905—1906刊《绣像小说》47—71期;?叟《学界镜》,1908刊于《月月小说》21—24号。
⑤⑥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⑦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三篇第二章“政变之分原因”、附录一“改革起原”、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70页、126页、137—138页。
⑧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115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⑨《说演说》,1902年11月5日《大公报》。
⑩参见《周作人回忆录》52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1128秋瑾:《演说的好处》。此文初刊《白话》杂志第一期(1904年9月),因错字甚多,这里用的是校正本,见《秋瑾集》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
1230上海知新室主人:《知新室新译丛·演说》,《新小说》20号(第二年八号),1905年9月。
1350《论中国宜遍设白话演说所》,1905年8月25日《顺天时报》。
14“伏查‘宣讲'二字之义,即日本之所谓‘演说'。今我国顽固士大大尚多憎闻‘演说'二字,彼辈不知‘演说'二字见于南北史,为唐以前之常语,而谬指为日本之新名词,可谓不学之甚矣。”
15《创设宣讲传习所议》,《宋恕集》上册415-4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16参见杨天石辑《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中国哲学》第一辑(1979)和第九辑(1983),以及王森《反西方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刘师培与“社会主义讲习会”》,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197—21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7其中商业类265,教育类103,政治类85,学术类65,外交类50,农业类、风俗类各26,青年类、艺文类各17,宗教类6,类、慈善类各4。参见张玉法《清末的立宪团体》90—144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
18参见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27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19《练习演说会之发达》,1904年11月9日《警钟日报》。20《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
21《敬告宣讲所主讲的诸公》,1905年8月16日《大公报》。
22这段文字,乃根据李孝悌《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杜,2001)65—66页撮要;另外,本节的论述,受李著第四章“宣讲、讲报与演说”的启发,特此致谢。
23参见《说宣讲所》,《敝帚千金》第二册,1905年9月。关于《大公报》附张《敝帚千金》,参见杜新艳《白话与模拟口语写作——〈大公报〉附张〈敝帚千金〉语言研究》,夏晓虹等著《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379—41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24参见拙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小说史:理论与实践》227—2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25参见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绪言》。
26《戏园子进化》,《北京画报》3期,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
27参见李孝悌《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09页,以及夏晓虹《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现代中国》第五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
29《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1904年4月25—26日《警钟日报》。此文刊“社说”栏,未署名,之所以断为刘师培作品,参见李妙根编《刘师培生平和著作系年》,《刘师培论学论政》48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31《论中国宜遍设白话演说所》,1905年8月25日《顺天时报》。
321;Ⅸ参见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日本近代国语批判》30页、41页、110—11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33福泽谕吉著、群力译:《劝学篇》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34“比如用文章叙述出来不大使人感兴趣的事情,一旦改用语言说出,则不但容易了解,而且感人至深,古今有名的诗歌都属于此类。”(《劝学篇》66页)“换句话说,就是借观察、研讨、读书等方法搜集知识,借谈话交换知识,并以著书和演说为传播知识的方法。”(《劝学篇》67页)。
35“近来社会上演说会很多,可以听到有益的事情,诚属有利,如言语通俗流畅,则演说者和听众双方均感便利。”(《劝学篇》98页)
36《文明论概略》第一章“确定议论的标准”中,谈到在鼓励不同观点互相碰撞方面,报章与演说所起作用:“有识之士所以特别重视人民议会、社团讲演、便利、出版自由等,也就是因为它有助于人民的接触。”见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3751参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14—150页、95—96页。
38任鸿隽:《前尘琐记》,《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708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39如柳亚子在晚清文坛很活跃,但因口吃,极少演说;严复、王国维学问好,也偶有讲稿传世,但远不及文章精彩。
4041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402页、450—45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4243参见《〈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7卷5页。44参见鲁迅《壬子日记》,《鲁迅全集》14卷6—10页。45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11卷308页。
46参见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李霁野文集》2卷29—3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47参见朱金顺辑录《鲁迅演讲资料钩沉》16—19页,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刊本,1979年。
48参见鲁迅《〈集外集〉序言》,以及朱金顺的《鲁迅演讲资料钩沉》和马蹄疾的《鲁迅讲演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49参见拙文《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5期。
52参见知新室主人《知新室新译丛》中的《弁言》及《演说》,《新小说》20号。
53黄炎培:《八十年来》,见朱有主编《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53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54参见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544页。
55参见宣炳善《大学演讲与自我启蒙》,《书屋》2005年8期。
56参见《复旦公学章程》第十六章《演说规则》(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及马相伯《关于震旦与复旦种种》(朱有珊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71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57参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1110、1151页。
58于右任:《追念相伯夫子并略述其言行》,1939年11月26日《国民公报》。
59参见《复旦大学志》卷一第2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60黄钰生:《早期的南开中学》,申泮文主编《黄钰生同志纪念集》39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
61参见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37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
62吴大猷:《十年的“南开”生活》,《国立南开大学》,台北:南京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
63参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301—309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
64闻一多:《仪老日记》,《闻一多全集》12卷41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65参见颜浩《千古文章未尽才——〈闻一多演讲集〉序言》,《中国》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
66参见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79年;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二章第三节“以拒俄为中心的学潮高峰”,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
67正如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所说的:“京师大学堂的拒俄运动,是北京大学上发生的第一次性群众运动,是北大学生运动的开端。”(31页)
68参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5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69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2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70参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上册20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580页。
71参见《平民教育讲演团广告》及《演说奖金条例》,均见1919年3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
72《雄辩会开会》,1917年12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73《北京大学雄辩会国语第一支部细则》,1918年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
74《雄辩会布告·北京大学法科雄辩会国语辩论成绩表》,1918年2月5日《北京大学日刊》。
75《改组雄辩会之提议·公启》,1919年3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
761919年3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刊《改组雄辩会之提议》;同年4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上有《辩论会开成立会纪事》。
77参见1919年10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所刊《辩论会启事》,以及同年11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的《辩论会通告第三号》。
78朱务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缘起及组织大纲》,1921年9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另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下册26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7986参见《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1919年3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
801919年5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所刊《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称新加入团员中有俞平伯;1920年3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分组单》中,第四组成员包括朱白清。俞平伯的生性沉穆不善言辞,可谓人所共知;至于朱自清,虽长期在中学、大学教书,同样不以演说见长。参见曹聚仁《文坛三忆》3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吴组缃:《佩弦先生》,郭良大编《完美的人格》16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
8188参见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106—114页、1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228—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82《平民教育讲演团报告》,1920年6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
83相关史料,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下册2601—2612页,以及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中1919至1923年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84《平民教育讲演团长第三次常会纪略》,1920年3月16日《北京大学日刊》。
85《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1920年3月30日《北京大学日刊》。
87与此相类似,辩论会刊行杂志的计划(参见1919年10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的《辩论会启事》:“拟自本学期起,除练习辞令之外,并发行杂志一种,以便互相讨论而为学术上之磋磨。”)似乎也落了空。
89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上册96—97页。
90《北大国语演说会、北大国语辩论会启事》,1925年3月16日《北京大学日刊》。
911924年11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北大国语演说会简章》,声明“本会以练习语言交换知识为宗旨”,会期每周五举行一次,聘请导师“以指导演说及辩论之进行”;1925年1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载有《雄辩会通告》:
本月4日午后7时在二院大讲堂开讲演大会,由陈启修、燕树棠、高一涵等讲授辩论演说之方术及理论,欢迎全体会员及校内同学参加。
92参见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262—26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93亚理斯多德称:“我们只讨论有两种可能的事情。至于那些在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没有另一种可能的事情,没有人拿来讨论。”(罗念生译《修辞学》2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现代中国史上的“辩论”与“演说”,其差异正在于此。有没有对手,允不允许驳难,涉及到开口说话时的心境与姿态。大部分情况下,居高临下的启蒙者,不允许、也没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
94平等阁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总批》,《新小说》2号,1902年12月。
95参见1904年4月20至22日《警钟日报》。另外,同年4月25日,《警钟日报》又刊出了六折优惠的“《演说学》折价券”,称“开通社会风气,以演说之力为最大,是书图说详明,颇便学者”。
96童益临编:《演说学讲义》,关东印书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冈野英太郎著、钟观诰译:《演说学》,广州:文明书局,1923年;冈野英太郎著、钟观诰译:《演说学》,上海:国光书局,1925年;汪励吾:《实验演说学》,上海:人生书局,1928年;徐松石编著:《演讲学大要》,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杨炳乾编:《演说学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余楠秋著:《演说学ABC》,上海ABC丛书社,1928年;郝理思特(R.D.T.Hollister)著、刘奇编译:《演说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程湖湘编:《演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徐松石编著:《演讲学大要》(“初中学生文库”本),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余楠秋著:《演说学概要》,昆明:中华书局,1941年;任毕明著:《雄辩术》,桂林:实学书局,1943年;任毕明著:《谈话术》,桂林:实学书局,1945年;任毕明著:《演讲·雄辩·谈话术》,桂林:实学书局,1946年。97陈源:《西滢闲话》335—336页,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3版。
98《〈胡适文选〉指导大概》,《朱自清全集》2卷209页、29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
99参见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此传撰于1939年,现收入曹述敬著《钱玄同年谱》作为附录;此处引文见曹著171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
1:Ⅰ如刊《中国白话报》第五期的《中国大家颜习斋先生的学说》、第六期的《黄黎洲先生的学说》、第七期的《王船山先生的学说》等。
1:Ⅱ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称:“此刻白话文应用范围,其实也尚只在报纸新闻副刊乃至普通著作之类。如要写一传记,白话文反不易写。如要写一碑文,用白话,实不甚好。有时连日常应用文字也不能纯粹用白话,不得不转用简单的文言。若我们要来写一部历史,如《中华民国史》之类,单就文体论,便有大问题。”(97页)
1:Ⅲ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Ⅳ周作人《〈燕知草〉跋》,《永日集》,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1:Ⅴ参见拙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四章“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Ⅵ参见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76—27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1:Ⅶ参见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及《国语文学淡》二文,均收入《与生活》,上海:群益书社,1931年。
1:Ⅷ参见拙文《当代中国的文言与白话》,《当代中国人文观察》121—1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1:Ⅸ据太炎先生晚年弟子沈延国称:“又先师曾谕延国云,昔在江苏教育会演讲,曹聚仁所记录(即泰东书局出版的《国学概论》),错误较少;而另一本用文言文记录的,则不可卒读。”参见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39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1:Ⅹ参见曹聚仁《章氏之学》,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175页,香港:学林书店,1971年;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55—5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
1;Ⅰ参见罗常培《自传》,《学人自述》268页,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1;Ⅱ参见拙文《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中国大学十讲》135—18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Ⅲ亚理斯多德著、罗念生译《修辞学》18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
1;Ⅳ《章行严先生莅雄辩会演说纪要》,1917年12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
1;Ⅴ《学术讲演会启事一》,1918年2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1;Ⅵ《学术讲演会特别启事》,1918年2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
1;Ⅶ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除总纲性质的《开讲日示诸生》《学规》《读书法》《通治群经必读诸书举要》外,主体部分按原典《论语》《孝经》《诗》《礼》《洪范》《易》来展开阅读与阐释,不受现代学科分类体系的制约。
1;Ⅷ1920年新潮社编辑刊行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被视为蔡先生思想学说“最好的结集”(参见周作人《记蔡孑民先生的事》和高平叔《〈蔡孑民先生传略〉叙言》,载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32—36页、287—290页)。此书共收文84则,大致可分为三类:演说40则,文章21则,序跋及书札23则。演说占主导主体(包括《劳工神圣》《以美育代宗教
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词》等),但专业性不强。集中不少演说,除注明登坛时间,还有何时修订成文。
1;Ⅹ《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1<Ⅱ参见葛继圣《中国速记应用的历史、现状、问题及建议——纪念中文速记创始一百周年》,《广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1<Ⅲ汤炳正称:“当时,应全国学术界的要求,每一门课讲毕,即将听讲记录集印成册。先生以精力不给,付印前皆未亲自审校。因此,在听讲记录出版时,他坚决反对署上自己的名字。”见《忆太炎先生》,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462页。
1<Ⅳ1<Ⅴ《通信》,《新青年》3卷1号,1917年3月。《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及《蔡孑民先生之欧战观——政教会欢迎会之演说》二文,刊《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
1<Ⅵ方豪:《马相伯先生文集·凡例》,《马相伯先生文集》,北平:上智编译馆,1947年。
1<Ⅶ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Ⅷ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自序》,《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1<Ⅸ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
1<Ⅹ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3页,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订正三版。
1=Ⅰ中书君:《〈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新月》4卷4期,1932年11月。
1=Ⅱ1=Ⅲ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47页及《序》,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1=Ⅳ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小序》,《中国哲学的特质》,台北:学生书局,1962年初版,1987年第六次印刷。
1=Ⅴ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一书《自序》,称“此稿乃一年之讲堂实录”;“亦有前后所讲重复,并有一意反复申明,辞繁不杀,此稿均不删削。亦多题外发挥,语多诫劝,此稿乃保留原语。虽非著述之体,然亦使读者诵其辞,如相与謦于一堂之上”。
1=Ⅵ近年风气大变,喜欢阅读“演讲稿”的大有人在。若北京的三联书店推出“三联讲坛”,“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缘起》),便博得读书界一片叫好声。至于像《钱仲联论清诗》(魏中林记)那样,“其中,评骘先贤时人诗文人品,思想言论,或褒或贬,‘随口而谈',‘思至语出',为存原貌,并未刊落”(《钱仲联先生跋语》,《学术研究》2004年1期),更是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