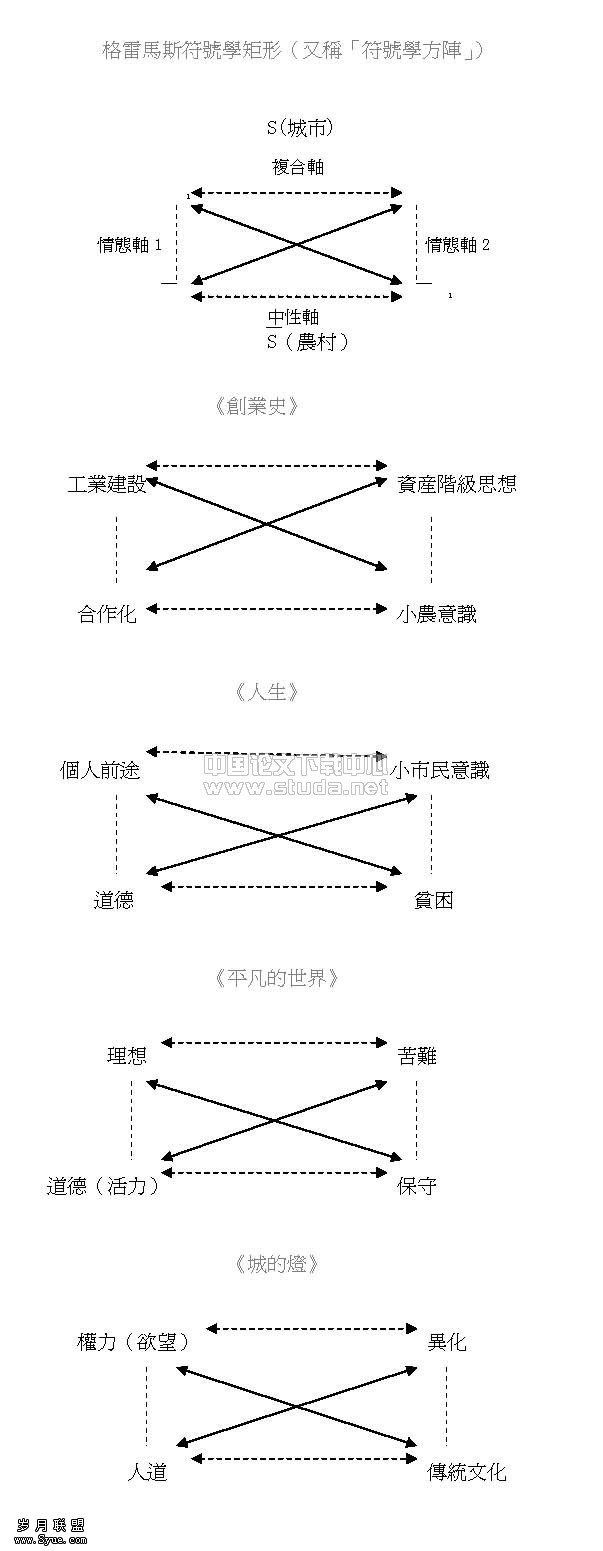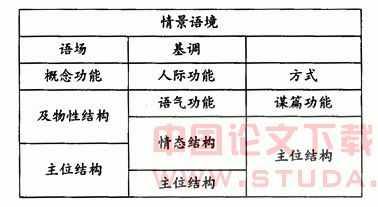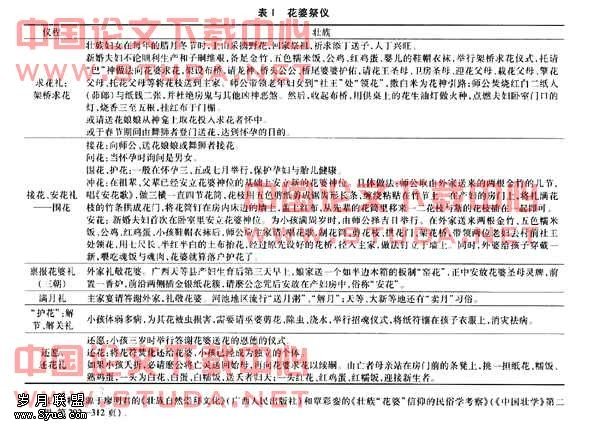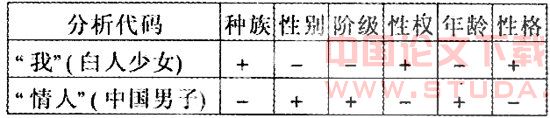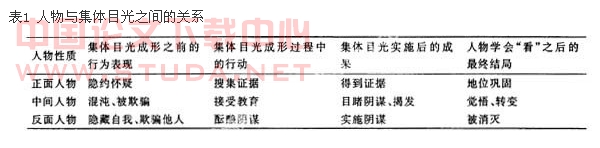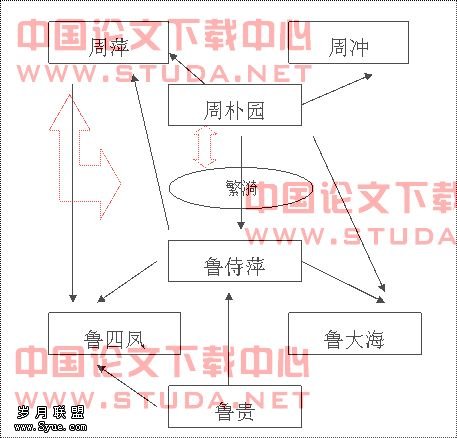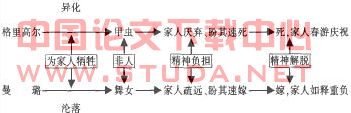“闲情与文学”研究论纲
摘要:闲是文明社会中的一种存在的生命现象。闲的审美化的源头是庄子。闲情作为一个观念的出现则在中古。当时陶潜、刘勰都提出了闲情之说,而刘勰将生命状态的适意、悠然命名为闲情,应是后世具有审美意义的闲情观念的源头。闲情审美是古代文人人格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化生命状态的具体展示。对这一观念及其相应特征的把握,对研究中国古代文人人格、中国古代文学内容形式的开拓及整个文学的发展、古代文艺学范畴和相关文论思想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闲情 审美观念 文学价值 研究纲目
“闲情”的出现,是在“闲”的观念成熟之后。闲,《说文》作“盻”,释云“隙也”。段玉裁注云:“隙谓盻,盻者,门开则中为际,凡罅缝皆曰盻……盻者,稍暇也,故曰盻暇。”从字源上看,在早期“盻”(下面一律写作闲)之含义更多地侧重于指空间,从空间移植到时间之宽裕上,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事。最早综合诸般闲的意义,进行必要的升华,使“闲”显示出一定美学品格的是庄子。《庄子》中屡屡提到闲,《天地》云:“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大宗师》云:“其心闲而无事。”《刻意》云:“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其基本含义是时空上的闲暇以及由此闲暇引申出来的安静无事。从此,对闲情这种观念而言,道家的尚闲“无为”和儒家的“游于艺”为其提供了思想的保证,儒家的“舞雩风流”和道家的“濠梁闲趣”为其提供了实践的探索,使其在魏晋六朝之际成型有了相应的基础。另外,佛学在当时表现了与世俗性情浓厚的附会热情,一则大讲就德修闲,二则对闲中之心理感受给予了理论上的支持,其法乐之说便是一个代表。法乐,缘自佛法中的触受说:触就是接触,它能使主体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这些感受共分三类,有苦受、乐受还有非苦非乐受,而所谓法乐,实则接近这种非苦非乐受。而这也恰是日常人生中所云七情六欲之外的一种微妙情感,从生命的本体考察,它是主体在现实世界之中的一种样态、一种体验;从哲学上说,它也是主体理解世界呈现自我的一种方式。这种样态、体验、方式最接近我们所论的闲情,这一点也对中古文人从艺术人生实践的层面感受认知这种情感提供了依据。
“闲”“情”二字联用在中古(6世纪前)最著名的有两处,一是陶渊明的《闲情赋》,一是《文心雕龙·才略》篇中的“谢叔源之闲情”。
关于陶之《闲情赋》,陶澍《靖节先生集》卷五作“闲情赋”,注云“何本闲作‘盻’,非。”李公焕笺注本卷六收此文,亦作“闲情赋”。“闲”与“盻”在《说文》中并有收录,“闲”训为防闲之意,非“盻”之闲暇意。又澍注云:“赋情始楚宋玉、汉司马相如,而平子、伯喈继之为定静之辞。而魏则陈琳、阮蠫作《止欲赋》,王粲作《闲邪赋》,应蠩作《正情赋》,曹植作《静思赋》,晋张华作《永怀赋》,此靖节所谓奕世继作,并固触类广其辞义者也。”从汉语特点看,古代除双声叠韵外,单字占了大多数,复合型的词组也不多见,故“闲情”与“正欲”、“闲邪”等一样,作动宾结构的组合,于情于理较合。钱钟书先生认为:“合观诸赋命题及此赋结处‘坦万虑以存诚’,闲情之闲即防闲之闲,显是《易》‘闲邪存诚’之闲,绝非《大学》‘闲居为不善’之闲。薛士龙《浪语集》卷二有《坊情赋》,亦此体。坊如《礼记·坊记》之坊,即防闲之防也。”[1]王瑶称:“刘叔雅先生据《说文》言‘闲’为防检之义,非闲暇之闲,则赋名与阮蠫止欲,应蠩正情同旨,更不能指之为瑕矣。”[2](辶录)钦立注《陶渊明集》、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龚斌《陶渊明集校笺》等都主此说。闲情如此连用,在中古可寻旁证,《宋书·王僧达传》引其《上表解职》云:“利伊恩升,加以今位,当时震惊,收足失所,本忘闲情,不敢闻命。”此闲情,即防情感放逸之意。依此看来,有的先生以《闲情赋》之闲情含艳情,近于宋人“谁道闲情抛却久”之闲情,亦近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中“或年光盛小,闲情窈窕”之闲情,未必合于唐前的实际。
谢混(叔源)之闲情,见于《文心雕龙·才略篇》:“殷仲文之孤兴,谢叔源之闲情,并解散辞体,缥渺浮音;虽滔滔风流,而大浇文意。”关于这个闲情,周振甫注云:“未详。孤兴、闲情两篇,都不合规范,因为它们宣扬清谈风流,使文意浮薄。”[3]这是字面对译,闲情为何物未明言。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卷十云:“按谢混之‘闲情’,除《文选》所载 《游西池诗》足以取证外,江淹《杂体诗·谢仆射》首专以‘游览’标目,亦可得其仿佛。’”《游西池诗》中云:“回阡被陵阕,高台眺飞霞。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冥鸣禽集,水木湛清华。褰裳顺兰禬,徙倚引芳柯。美人愆岁月,迟暮独何如?”因感岁月匆匆,故而恣意遨游,高台陵阙,惠风白云,加以清景鸣禽,水木清华,悠然闲适,因思良友与共,故李善注云是“本思与友朋相与为乐”之作。而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中之《谢仆射混》一首,不仅以《游览》标目,而且其内容也是流连光景的闲适。如此看来,谢混之“闲情”已不同于陶之“闲情”,乃是闲暇悠然之情,与今日之理解已很近。而实际上,此意义的概括者当属刘勰,是他首次将谢混悠然适意的游览流连命之曰闲情。因此,本文作为美学范畴引进的闲情,其本源不在陶渊明的《闲情赋》,而在刘勰的《文心雕龙》,它在六朝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以六朝贵族山水登临、诗文风流、清谈雅集的艺术人生实践为基础的。
那么,闲与闲情审美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通俗地说,因闲而破闲,有闲而思遣,爱闲而欲假物以扩展、寄托、驻留的过程就是闲情。它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种生命状态,一个过程。具体说来,能由自我支配的、不受外力干扰的时间都是“闲”,而追求闲、妆点闲、享受闲、描绘闲、转移驻留闲的情感活动过程以及这一情感活动的固态结晶如文学艺术品的创作等等,都是闲情。它是超越人本能的基本生存需求之外的一种使生命更丰沛、姿致更优雅的情感状态和生命状态。其实现的手段,就是通过寄的形式,将心中的这种情感或情感期待物质化、固态化、实践化、形式化,从而实现主体与社会、自然的沟通,唤醒生命的归属感与统一、同情的冲动。它涵摄着主体物质供奉的美化、主体精神格调的美化、客观对象的美化以及主客关系的美化。
与闲情相关的研究在西方早在上个世纪初即已开始了,如美国凡勃伦创立的“闲暇社会学”等,但研究集中在学、社会学的领域。德国学者约瑟夫·皮珀的《闲暇文化的基础》,则侧重于从大文化上思考闲暇。中国古代文人的闲情与西方所谓闲情的内涵差别很大:西方侧重指空余时间的消遣与价值转化,其核心是西方传统思想中人与自然对立观念下的带有征服与功利色彩的物质性浓厚的行为,与消闲基本上已经一体化,而这种目前被我们广为接纳与倡导的休闲,一如西方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其被动的娱乐和严密组织的群体活动具有压倒一切的支配性,创造性的活动则少得可怜。我们本民族传统意义的闲情是一个美学范畴,是对古人闲适闲逸情感的概括,它更多的与心灵世界和艺术发生关系,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物。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也比较零散,且存在以下不足:
先是学术讨论的逻辑起点没有深究。很多研究者在对古代文人的艺术化生命状态以及相应的追求做出描述时,都把闲适等与闲情审美相关的观念视为一种前在的、默许的存在,事实上学术界从未对其从理论上做出界定,未从观念沿革的角度对其做过清理。
二是个案的展开比较多,且以茶、酒、园林、隐逸为主,而对中国古代文人众多的带有闲情审美色彩的范式诸如雅集、清供等关注不足,且流于现象的描述;典型对象集中在陶渊明身上,但由于对陶渊明田园模式在六朝地位过分的推崇,致使忽略了从魏晋六朝开始,很多文人贵族在闲情审美的认识与范式的开拓上都有相当的贡献,且流风远播。加上有的学者视闲情为艳情并以之为贵族腐朽情趣,使我们的学术研究遗落了古代文人主流更丰富的艺术化生命状态追求与寄托范式探索,并使古人闲情审美的博大内涵被缩减。
三是研究多偏于文化的梳理,对闲情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缺乏研究。此前偶有涉及,但不成系统,尤其缺乏从审美观念与文学关系上的系统把握。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学者提出了“经济生活与文学”这一研究范畴,其中一些观点和研究思路开始涉及到部分闲情内容。不过这一研究范畴傅雷先生很早之前就已经注意,他在丹纳《艺术哲学》译序中就明确提出,丹纳在考察影响艺术的诸般因素时,所重视的都是上层建筑,却忽视了最基本的经济生活。事实上,人类文明所负载的一切均可能对文学产生影响,但影响力却有主有次,最主要的是,类似经济生活这种文学本体之外的影响一方面以一种综合的外力体现,另一方面则不可能直接作用于文学,它需要中介,这个中介就是审美观念。从与文学创作和作家接近度上看,价值观念近而其它因素远;从学理上衡量,恰恰是离文学更近的这个视域,因为其向外来源于各种非文学因素的定型,向内直接作用于文学创作,所以它才应该是文学研究的主要描述对象:闲情审美就是这样一个观念。
从以上研究现状衡量,闲情的研究是一项填补美学文艺学范畴研究空白的工作,其中关涉的内容包括古代文学艺术的创作,古代文论以及文学思潮,文化风尚,古代文人人格建构等。这种研究,从综合性的高度入手,看似边缘,实质符合审美超越性的理论内涵。如果从审美观念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考察,闲情作为一个美学范畴与观念的研究在文学上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闲情与文学创作关系;“闲情文学”;闲情与文艺学范畴的开拓。
闲情与文学创作之关系的研究
这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研究领域,从闲情和士大夫或作家的人格、情趣的关系到闲情与具体的文学形式和文学表达内容的开拓等都有值得关注的话题:
1,闲情与文学表达空间的拓展。闲情审美观念的出现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表达空间,包括向外的开拓,即题材的开拓,比如琐屑细小之物纳入描写,自然山水纳入描写等;还有向内的开拓,即情感的开拓,比如奈何闲愁之情,流连光景之情,游戏消遣之情等。而向内的情感开拓则是闲情对文学表达更重要的贡献,也是题材得以开拓的前提,可以说文学真正意义的个人抒发是在闲情审美观念成型后出现的。
最先纳入文学描述视野的是创作主体的基本情志,其时情志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代,以诗大序为代表的文学理念成为主流话语,成教化、助人伦、美风俗是文学的核心追求。中古时代,情、景二端作为创作题材都已经完备,就景而言,山水作为审美对象进入文学表达,与此相关的田园也进入诗歌的讴歌范围;《玉台新咏》中的诗篇则把细碎、琐屑、香艳一概纳入笔端,与山水田园等一起印证了六朝文学中充盈着的流连光景情趣。其时文人性情挥洒,多是对流连光景细致丰富的演绎,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序中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便是它最高的概括。这个概括在中国历代文人心里获得了巨大的共鸣,明代山人将其名为清雅之事中的“四子目”,与花典、香禅、茗谈、觞政等具体的清课对应,虽有山人强作雅态之意,也是雅的透骨。心与物色之间的如此冥契,使物色光景成为文人们点化生命超越凡俗的不可或缺之物。对流连光景更高的美学提升是中古以后文人心态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情愫:奈何。
奈何之情与忧生之怀从本源上有着相通性,但从情感演革的基本规律以及魏晋南北朝文人敏锐的心灵感受记录考察,其时文人已经完成了对忧生之怀的超越,使奈何之情具备了审美的意义。具体说来,忧生是本能的且与自我的功利密切相关的一种对生命前途的恐惧,是生命自觉后无法安顿茫然灵魂的发泄与感叹;奈何之情则具有了反思的色彩,它将这种生命之痛在现实人生里通过现实之爱反射出来,使忧生的切实之痛被玄远的、朦胧的、无法言说却又流连于眉头心上的一种情感替代,这种情感有共同体的通感,有类的共鸣,它虽肇始于切身之感,却又有着自我之上的终极意义的感喟。《世说新语·言语》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桓公北征,径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冯友兰先生分析道:“真正风流的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够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所以其情都是对宇宙人生的情感,不是为他自己叹老嗟卑。桓温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他是说‘人何以堪’,不是说‘我何以堪’……桓温卫筁是说他们自己对于宇宙人生的情感。”[4]冯先生这里讨论的这种无可如何的对宇宙的情感,就是奈何的一种表达方式。他揭示了奈何作为一种文人对宇宙人生所生发之情感对自我本能之意识的超越性。在对命运之限度等充满遗憾的情感交织里,委身顺从的瞬间,回眸牵挂;在已逝、未逝、将逝之际伸手婉留。个体无力以整全、永恒的姿态去面对整全与永恒的美,但心灵却在瞬间能完成对这至美的瞩望。心中的期待与生命真实的获得之间往往在可望不可及、可暂不可久之间造成多愁善感文人心中强烈的落差,此落差又因当下之美的深切感受而被加强:知其美,而不能全部拥有;知其美,而不可天长地久。这种情感,将人之自觉、生命的自觉提到了寻求一种更深沉人生态度与精神境界的高度,“它是玄学所指示的人生归宿,它是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大化之境。极度的痛苦、骚动,凝成了极度静谧超然的审美意境。”[5]
无论是流连光景还是奈何之情,都是在贵族文人中广为渗透流布的一种贵族气十足但又绝不能与颓废相提并论的对人生宇宙的情感。这是一种无关生理痛苦主体利益却关乎生命之珍惜的惆怅情绪,文人们悠闲平静地审视和捕捉属于心理结构深层次的悸动,是地道的闲情。这种情感作为一种审美情感在中古的成熟,使这种情感的表达提上日程,而当时文人书写“赏际奇至”①的追求就是使这一情感与创作之间建立相应关系的理论的支撑。文学作为奈何之情的表现形式,使文学表现情感的深度与广度得到极大扩展,诸如感离别、念绮情、伤春、悲秋、叹逝、怀旧等等情怀,自魏晋南北朝开始,便成规模地在文学作品中亮相。
2,闲情范式与文学。范式最先被美国哲学家库恩用来解释科学革命,后被美学界广泛借用。美学在吸纳范式这个命名时,摈弃了其中作为规范而起到的一种约束作用,吸纳了其作为模式对他人的启示和辐射意义,并使其适用范围突破了单纯的理性升华。美学范式有两个重要特征:具备对范式进行把握的非理性手段——情感;具备可模仿的特定之模式以及对模式的信念,模式本身因人而异的内在生发机制使之历久弥新。从这个意义上分析中国文人的生活与创造,我们能拈出一大批范式:诗酒风流、品茗、以文会友、雅集、清谈、登山临水、田园耕读、清供、雅玩、园林卜居等等。这些范式,是在贵族闲逸人生追求的实践中与寄的观念同时发展、成熟起来的,它们都是有意义的情感形式与符号系统,作为一种情理结构,它们是的积淀与主观情感的整合;是闲情或艺术化生命状态在现实人生中展开的重要形式,也是主要内容。由于寄是为情感寻找适当的表现形式,所以这个适当的形式在寄的审美观念里占有重要地位,它就是审美的范式。从魏晋六朝开始,中国文人对寄的审美范式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并充分体现在现实人生当中,这是寄的审美范式确立并得以在广大文人的艺术生活中贯彻的基础②。这些范式之中,田园与山水以及园林是文人关注的焦点,但多从文化的角度观照,有待于研究视野的拓展。其它闲情范式关注则显得不够。
以诗酒风流为例,它是对中国文人诗、酒之爱的概括,过去对酒的文化研究很多,但其和文人和文学的关系尚未有详细解读,如果联系魏晋时期酒风高涨对当时生死、游仙、隐逸、闲适等文学主题的影响,结合陶渊明、李白、苏轼等文人诗与酒的关系,结合刘熙载等对酒境与文境关系的论述,酒与文学就成了深化古典文学研究的又一条路径。诗酒结合而形成的诗酒风流并未取代诗和酒彼此单独的范型意义,恰恰是彼此在各自领域对文人艺术人生寄托的贡献,才形成了后来的融合。晋宋以后,纵酒狂欢的文人风气被艺术化的雅适所代替。诗文的无用观与饮酒之境与道的成熟,使诗文与酒这两种闲情要素的结合有了基础,诗酒流连也随着诗和酒之审美意义的凸现而逐步成为文人重要的闲情范式。《梁书·江革传》云:“(革)除光禄大夫,领步兵校尉,南北兖二州大中正,优游闲放,以文酒自娱。”《陈书·文学传》言阮卓:“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会,改构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宾友,以文酒自娱。”文酒自娱和诗酒流连是一体二象。在六朝以后,此类飞觞醉月逸兴遄飞辅以诗文的优雅,基本成了文人的主流。诗与酒之间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二者更细微的互动关系以及对中国文人艺术人格的塑造等等有着丰富的可阐释余地。
雅集是中国古代文人一种艺术化的聚会形式。它以志同道合为人员的选择标准,以艺术素养为与会人员的基本要求,以艺术的创作与赏鉴作为集会的主要内容,凭依着良辰美景,辅助以美酒佳肴,追求内心的赏心乐事。概言之,以文人为主体、以闲情雅致为追求、以幽雅的环境为依托、以酒肴等物质的保障为基础、以艺术为手段、以平等的友人身份交流的无目的的文人集会就是雅集。它是中国文人重要的生命投入与情感寄托形式,也是一种颇具民族特色与优雅魅力的文化形态。自从曹魏文人邺下西园之集开始,中国文人便对雅集表现了巨大的热情,金谷集、兰亭集且不论,它如唐代文人“雅会襟灵,琴书相得”、宋代的元?文人雅集、元末明初东南文人雅集、明代苏州文人雅集与台阁雅集、明末清初文人的结社、清代的文人选名园、开高会、一时文宴半江南等等皆是。最能说明后世文人雅集热情的,是雅集一类的图画在文人中广为流传且数量庞大,如五代就有《姑苏集会图》、《林亭集会图》;北宋时代,苏轼、米芾、黄庭坚、秦观等文人聚会附马都尉之府,传说李公麟创作了《西园雅集图》。随后,以此为题的画作历久不衰,南宋僧梵隆、赵伯驹、刘松年、马和之等皆有创作;明代的仇英、唐寅、陈洪绶等十余人,清代石涛、王云等二十余人以及近代张大千等人,皆创作有《西园雅集图》。一个雅集的题材在文人中如此流行,说明雅集这种文化形态的代表性以及与中国文人情感寄托需求的契合。更为主要的是,雅集当中飞觞醉月天人合一的境界以及清谈、鼓琴、赏帖、泼墨挥毫、吟诗作赋等闲情寄托手段的投入,对中国文人的人格塑造以及中国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因此,这个文化形态不是一种浅薄的闲适,它是士大夫情趣挥洒、艺术创作、技艺切磋、风流播布的重要形式,超逸格调对物化的疏离以及与自然的亲近、尚文尚雅等精神趋向以及综合各种闲情寄托手段的集大成的形态,使雅集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密切而具体,从历代雅集的历程变异的梳理到雅集具体形态与不同时代文学思潮的关系、从雅集之中寄托手段对艺术的影响到雅集与文学团体之关系、文人人格之构建等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另如琴棋书画,六朝时期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篇》首次将其列入文人该具备的本领。这当然代表了作者个人的人格设想,但同时也是对当时文人风尚的。当时文人,几皆以博综为追求,以杂艺自饰。这一时期,经过与文人之间漫长的互动,这四项艺能逐渐在六朝之际实现了一种整合,并在后世以一种集体的面目被人们标尚,成为中国文人艺术人生与风流面目的表征,琴棋书画,在这样的推崇之中,甚至具备了一定的人格意义,完成了与文人的一体化。在文人的情感寄托中,“琴棋书画”对于主体的主要意义在于:娱情与展示玄意人生。此外,这几种玄意人生道具在闲情人生的追求里,都与文学的理论、意境甚至手法相关。如《文心雕龙》、《诗品》就明显受到乐论、书论、画论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局限于棋品、书品、画品形式对文学批评的影响,相应观点对文学的影响,也不局限于相应的艺术批判范畴术语对文论的渗 透,还表现在更为具体更为细微的影响上,如文学的评介里直接渗透了书法的标准,《文心雕龙·练字》一章云:“是以缀字属篇,必须练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暗淡而篇?。善酌字者,参伍单复,磊落如珠矣。”刘勰这里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思想:在文学之鉴赏的标准上兼包作为艺术的书法,这是中古文人很重视但却被后世研究者忽略的一点,也是我们民族文学中所独有的。另如文人所精之乐器与诗歌风格的关系;以琴的优雅惆怅幽邃深远和笛的嘹亮穿透悠扬为代表的意象的解读;画和诗文结合的题画诗、题跋等的研究;琴心、画境、文心、棋品融合互动最终统一于文学的路径等等都有探讨的必要。
3,墨戏。墨戏过去主要用来指绘画当中尤其是文人画当中的一种兴到之际的自由挥洒。著者在此借用,主要是针对文学创作中的游戏消遣之作与心态而言的。有三个突出表现:戏作、拟作、酬应。戏作就是游戏、幽默诙谐之作,关系到很多文学形式的创新以及文体与手法的互渗,也蕴涵着不同时代文人的心态。拟作之中,首推拟古。汪师韩《诗学纂闻》评陶渊明《拟古九首》云:“今观唐以后诗,凡所谓古风、古意、古兴、古诗,与夫览古、咏古、感古、效古、绍古、依古、讽古、续古、述古者,都不知其所分别。”但多与拟古有关联。另有代笔,即模拟他人的身份、情感、性情、声口,表达彼此之间的情意。以自己的口,说别人的情,是典型的为文造情,萧衍《代苏属国妇》、萧纶《代秋胡妇闺怨》、王僧孺《为人伤近而不见》、《为姬人自伤》等等,揣人肺肝,代人喜怒,亦多百无聊赖之寄托。但拟作何以历久而不衰、不同时代模拟对象的变异中折射出的文人心态和文学思潮、模拟之中的艺术创新、拟作的价值评量等等,都是深入解析文学史的视角,并非一个百无聊赖所能涵盖。而江淹拟古之中寄象出意,以作代赏,拟作与文论之间的关系以玄学方法论的形式得以显现,其具体的关系有待揭示。尤其魏晋六朝之际,拟作风行,其发生的根源与当时文人普遍接受的“拟诸物宜”的文学观念有关,是中国式的“模仿”理论支配下的产物,对此的论述,将深化对古代文人创作理念的了解。避免简单的价值评判。
酬应起于曹魏之际的邺下之集,兼包着应酬与倡和。应酬多因事而发,倡和则多因人而和,其最初的发端是与文人侍从性地位相关的。曹魏定都邺下,收揽天下才士,形成了邺下文人集团,其主要的作用,即是侍从太子等游弋于台榭、雅聚于西园,上有兴感,即命为诗赋,这即为酬应。沈德潜评应璩《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一首》云:“魏人公宴,俱极平庸,后人应酬诗从此开出。”可备一证。现存曹魏文人的诗赋,有很大数量属于此类。
奉和这种形式,因文人附庸性地位在现实中的延续而延续下来。一方出题,一方援笔,一方付出闲适,一方付出才情,以我之笔,造他人之情,双方合作,共同营造了闲情色彩极浓又非常风雅的文人生活氛围。奉和、命作的形式,是倡和的早期形式,它显著特征即是:一倡众和。魏晋之后,和的形式下移,逐渐成为文人彼此之间附庸风雅、雅聚寄兴的手段,因纯属性情所致,亦为生活点缀,无命令相加,无身份悬殊,所以更为自由不拘,倡和的时代,算真正到来了。如唐代元稹白居易之间的倡和便历来为人称道:以上系此倡彼和。又有遥和,这种倡和又极关乎人情,寄情于诗,千里相寄,本无要事,只求一吐心胸,古人雅逸闲适,正在此中。甚至平常的赠答诗也属于酬唱一类,此类作品以汉代秦嘉徐淑的赠答为最早见,有学者做过基本统计,在全唐诗中,此类赠答诗就占了一半。
关于酬应之类诗文历来评介很低,叶嘉莹命之曰舞文弄墨,且评云:“舞文弄墨咬文嚼字,这就是诗人的坏处。有的时候,他的感情并不充足,却也能写一篇漂漂亮亮的诗,这就是舞文弄墨。这种舞文弄墨也是从建安时代才开始的。从建安时代,就开始有酬赠的诗。”[6]叶先生所言当然有理,可问题在于这些今人语境下的评判标准,根本与古人文学创作的主旨有悖:今人动辄讲文学艺术的纯艺术价值,而在中古文人眼里,文学尤其诗却是言志遣兴寄情的手段;其酬应,正是艺术化生命状态追求的体现。其它的游览、行旅、公宴、祖饯(送行)以及喜丧庆吊之类的应酬之作都面临着这样一个价值估量问题。受闲情审美的影响,在以上酬应之外,即情、即事、即目、即兴、即景的创作蔚然成风,成为古人创作之大宗。比如题壁——无论驿站、僧房、旅舍,虽有一时感慨,但更属当下的兴会,一个“即”字,也是有着丰富美学内涵的。
关于闲情与文学之间的宏观与微观话题还有很多,比如文学动力的研究。从历代文人钟爱闲业的角度衡量,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闲情是推动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延及唐代,世家大族逐步式微,中国的文学如闻一多所云从贵族文学、宫廷文学过渡到士大夫文学,闲情作为一种审美范畴与观念得到扩散,其对文学的推动便逐步演化为了中国文人演绎自我艺术化人生追求的自觉。其它诸如与创作繁荣并兴的文学阅读或文学“消费”的高涨、创作与“消费”的高涨与文学出版传播以及中国文人存留翰墨好闲爱文文化形态的奠定,等等,都与闲情密切相关。此外,由此衍生的品评走向文学评学理论的过程之中闲情对其内涵形态语码范畴的影响、历代侍从体制这一帝王闲情代言机构的体制演革以及对文学思潮的影响等等,都需要我们摆脱过去对贵族闲情逸致过多的批判意识,从历史价值上衡量其效用,并力争复原各种具体的情趣具体的政策态度与文学兴衰的关系。
又如文体的发展创新与闲情的关系,我们在注重文体内部沿革规律之余,不能忽视士大夫闲情审美的推动。以词的发展为例,学术界关于其发生与发展的说法大体如下:或曰六朝时出现,杨升庵《词品》、毛西河《词话》并主此说;或曰出自唐人绝句,南宋王灼《碧鸡漫志》、朱熹《朱子语类》、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即是。罗庸先生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这个基本上已经为学者普遍接受的观点,即音乐的转变是一个重要内因。但早期文人长于此技者如白居易等当时只填数调而止,原因是“盖与文人身份问题有关,不屑为歌伎填词耳”,“迨飞卿出,始大胆流连教坊,不顾身份,遂有若干新调之增加,实则为大胆利用民间小曲而制新词者也。此一现象之形成,不在词调之转变,而在文人身份之转变。”[7]罗先生此处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词与音乐的关系,可以称之为正本清源之论。只是最后的总结以为词调从少至多的变化出于文人身份的转变有些不确,事实上,温庭筠不再似以前文人那样顾惜身份,流连于教坊,无非是审美情趣的一种转移,这种情趣,恰是闲情审美之中接近艳情的那种内容。词之源头的曲子——无论大曲还是小曲,在一定的礼仪内涵之外,都是闲情的产物;而词调的发展,又与文人闲情的审美相关:由此可见,词的产生与发展与闲情是分不开的。其它如小说、传奇等等莫不如此,最典型者当属小品,小品从内容到文人情趣、从语言运作形式到文人自在的心态、从涉及文体的广泛到涵蕴知识的庞杂、从对载道致用的悖反到生命情调的挥洒,都能找到与闲情审美相关的迹象。而基于以上观点,历代文人勾栏瓦肆、青楼楚馆的徜徉以及由此派生出的艳情之作,以及和此近似的历代雅士与高僧大德的交游以及唱和,等等,都有着艺术价值之外的文化史文学史意义。
即使是文学创作之中的具体手段,也受到闲情的影响,从而将一种闲适悠然从容不迫的心态渗透至作品之中,中国的文学里于是出现了一般文采装点之外的闲笔,闲笔多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在要旨之外游离的“无用”之笔;紧张节奏下的舒缓之笔;兴之所致笔不由己的顺势游行戏娱之笔。这些闲笔,如同林语堂称颂的便装少女,韵致就在微微蓬松的发、尚未全掩的衣上,那是一种率真而不入规矩的真美。闲笔自然不是从魏晋南北朝时代才出现,但成为文学中之一大景观,却是由此才开始。闲笔具体的发生及演化、闲笔在不同文体中的表现以及作用、闲笔运用中所体现的文学价值以及所彰显的文化价值的研究,对了解中国文学自觉的历程、寻求自觉的标志、探索各种文体文学化的路径等都有重要意义。
“闲情文学”的专门研究
古代一向有按照题材、内容为文学创作分类的传统,《文选》先以文体分类,继而在其下又以内容分类,如赋下有京都、纪行、宫殿等;黄宗羲讲过台阁文学与山林文学;袁行霈先生将文学依据内容以及其发生土壤环境分为四类:宫廷文学、士林文学、市井文学、乡村文学。而依据闲情作为一个审美范畴与审美观念这一前提,以历代文人的创作为依托,“闲情文学”便成为一个文学类型③。
所谓“闲情文学”,是指以遣兴娱情为目的,以诸般文学形式为寄托手段,以非世用的与闲情相关的对象世界以及对此世界的即兴感受为内容的文学创作。
闲情文学和作家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心仪这一题材之文人呈现出一定的阶级差异,但又并非贵族的专利,而是表现了超越阶级的趋同性,只是不同阶级在对闲情文学表达对象的选择、对闲情感觉审美之妙处的把握以及心态上有着很大的差异。闲情文学与时代相关,但不是一般想象的与时代共浮沉,治世与乱世和闲情文学之间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大一统时代的闲情文学与偏安时代的闲情文学比较,偏安时代文人们往往表现出远较一统时代旺盛的闲情文学创作热情和开拓精神。闲情文学与文学地理相连,首先,闲情文学的光大与江南地理特征密切相关;其次南方与北方文人在闲情文学的创作上存在着审美价值单向流动的特征,即北方文人的闲情文学创作有着很浓的对南方的情结。在闲情文学与地理的关系之中,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即历代文人闲情文学之中存在着对个别名胜强烈的认同趋势,因而相关作品就呈现出空前的繁密。如晋人眼中的山阴道、六朝金粉下的秦淮河、唐代长安的曲江与春风十里三分明月占二分的扬州、宋代以后的西子湖还有范围更广泛的杏花烟雨中的江南等等。这种现象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更重要的是,它指示着中国文人的心灵归宿,其中带有皈依朝宗意味的徜徉与流连,可以使后人对中国文人的情怀深处有更深刻的理解。如今有学者正从事的“西湖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方面的一种探索,当然,这种探索应该放在文人整体与文人情怀心态的背景下观照,不能流于单纯的地域文化研究。闲情文学的类型、表现形式、基本定位、基本审美特征、发生的 源头与流变是构成闲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闲情文学的表现形式又以闲情审美是如何在不同文体之中实现并获得完善为重点;而在闲情文学的流变历程里,大一统的唐宋明清与偏安的六朝、南宋以及晚明这两条变化线索是其中的关键,对这两种时代闲情文学的总体特征以及相互影响的研究,可以对此前一些研究者所讲的盛世文学和衰世文学作出一些更具体而深化的补充。闲情文学的意象研究是这项研究中重要的一环。中国文人的闲情审美,是深深植根于农业文明自然的,其中众多的意象充满了农业文明下特有的和平温馨与淡泊,挖掘不同闲情文学意象与小农经济的关系,可以复原我国古代文学在生命意义层面的价值与意义。这种审美观念所带来的文学上的变革,就是诗人可以近距离地抵近农业文明意象,在人人习以为常的背景里挖掘陌生化效果,使在身边寻找诗意成为现实,并将日常生活诗化。将日常人生诗化的意思,一是在日常人生中发现诗的意味、化的活源;另一方面,则是将日常人生的意象大批纳入诗篇。前者如游弋、酌酒、读书、雅集、盥濯檐下、采菊东篱、斜卧南风窗下、带月荷锄归等等。后者如村舍、豆草、桑麻、穷巷、荆扉、桃李、榆柳、南野、方宅、草屋、夕露、孤云、飞鸟、青松等等。如结合历史特点分析,还会发现通过这些闲情意象所组织起来的境界与小农经济影响下的人生境界也是接通的,闲情之描述里屡屡有类似“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等对空间时间的具体细致的限定,以及在一定限定下的放逸和逍遥,这是自足产生的物质环境,只有心境的翱翔,少有物质的压迫。放在更具体的进化路径上,我们还可以留心闲情意象在与城市文明、商业文明接轨时所具有的特征,以及二者与纯粹农业文明意象的差异;关注经济发展商业文明城市文明发展浸染下文人对旧有农业文明意象的态度以及这些意象内涵的细微变异。
另外,“闲情文学史”的研究是“闲情文学”研究中很有分量的一部分,它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实现对中国文学的梳理,把文学史的研究从泛化笼统向具体明晰推进,由综合文学史、专门文体文学史、地域文学史向文类文学史延伸,只有这样,才能为综合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依据。尤其有意义的是,这个梳理可以不仅仅以古代文学为对象,而且可以打通古今,将古代、、当代作家作品纳入这个视角之下考察,这不仅具有学理上的可操作性,而且对探索我们民族艺术之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具有相当的意义。从现实意义和价值衡量,这也是一个致用的研究话题。目前一些学者在探讨“中国文学中的民族精神”,笔者在《文艺报》(2005,2月3日2版)也曾以“走出自我解嘲——关于文学研究的思考”为题,对这个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大致观点是:文学在历史上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培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凝铸了其中的道义内容:爱国、忧民、舍生取义等,但这并不是民族精神的全部,我们还应关注从文学中所呈示的、融合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那种虽非道义大节却恒常执着的现世性日常化追求——比如古代诗词小品中表达的以闲情审美为主要内容的日常生活艺术化追求和艺术参与下的日常生活运行,它发源于贵族却普泛于文人主体,是个体与群体与自然与社会相统一的人生境界,也是美的境界,是活生生的常态。它也许没有道义内容崇高,但也并不低俗,它所表现的对物化与粗俗的抵制和对僵化的冲击对和平的祈祷,是精神文明、文化建设的根本意义所在,同样是我们的文学研究应当更多关注并给予系统的。当现实的恐惧、罪恶、怨悔难以消磨之际,艺术恐怕是唯一的不丧失感性热情的救赎,其中闲情文学虽然难以实现自我的彻底拯救,但却可以在古人的闲逸悠长之境界中实现自我的逍遥与脱俗。“闲情文学史”告诉我们的是,历史上曾经有这样的艺术存在与人生追求。
闲情审美研究对文艺学范畴研究的开拓
闲情的研究首先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且具有一定的范畴研究的色彩,这种范畴因其与艺术化生命状态密切的关联因而具有观念的性质。闲情审美的观念,不仅贯穿于文人日常人生的艺术化追求、人生理想,而且还贯穿于文学艺术创作题材、文学艺术创作旨趣情调、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一个观念能在人生、艺术两方面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说明此观念是建立在人生、艺术之上的能进行再次抽象进而能实现对人生、艺术超越的,它是艺术,即美学的范畴,因其与文学艺术密切的关联因而同样属于文艺学范畴。从审美意识与审美观念结合的视角,探索儒道主流文化话语之外的一种闲情审美观念,本身也是对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一种新的开掘。具体而言,在拙著《闲意悠长:中国文人闲情审美观念演生史稿》中被论证为闲情审美观念确立之标志的寄和无用等都属于这个范围。
1,寄。作为审美的范畴与观念,寄在与文人现实人生接轨的时候,处于主体心灵愿景与人生实践之间的独特沟通路径上,也就是说,文人的任何可以称得上是美的情感,必须通由寄而与主体之外的客体发生关系才能生成。审美活动是情感的流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存在着一条从情感发生到情感维持与享受的轨迹,它以主客之关系为基础,以感而兴为起点,以赏会为收获。虽然审美的感觉往往以混一状态下的自我感觉为主,但事实上自我的感觉根本不可能离开客观对象。有的学者认为在对审美的研究中由对象入手分析审美现象是对中国古典美学精神中天人合一主旨的悖离,是西方美学研究物我对立观在中国古代语境之中的附会。但审美现象作为对自我向自我之外时空延展的形式的概括,在发生形态上必须具备与主体同时存在的客体,具备主客形成密切关系的条件,而混一的感觉只不过是一种审美意义上对客观对象的暂时忘却与忽略。在我们的美学或文艺学研究里,从感到兴都不同程度地引起过学者们的兴趣,如胡经之主编的《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里,感物、感兴被列入创造编,兴会被列入接受编,皆是将其列为了文艺学中的典型范畴。而作为一个情感运动过程中的不同状态,从创造至接受,从一种范畴到另一种范畴,从感兴到赏会,事实上是有中介的,这个中介,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寄。从美学的体系上说,中介也应当属于美学研究范畴,而这一点,恰恰是以前我们的美学研究或文艺学研究所忽略的。
寄是情感表达方式的寻觅过程、创造过程以及在寻到情感表达方式并积极投入其中时的生命状态;是在对象之中发现自我、实现物我契合从而提升对象与自我使彼此同时获得美化的一个审美过程。寄需要假物,反对心灵的枯寂与宗教意味的发遣,它是在与外在世界沟通交流之中达成的审美境界,是在与物的关系之中实现的自足;寄假物却不役于物,外物在纳入寄这个美学范畴之际没有功利。与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文学艺术,是艺术化人生的追求以及为了实现、完善艺术化人生而被美化了的自然、山水、园林,还有一切与文学艺术相关的创作、赏鉴以及交流,它向一切具有艺术韵味的形式以及形式的探索与创造开放。寄处在感兴赏会的情感链条上,是连接感兴与赏会、实现审美情感驻留的中介,是它激活了生命本然的热情,并使之得以延伸。其核心的内涵可以这样概括:在艺术人生的追求之中,艺术形式与审美感受之间属于多一同态对应,作为审美范畴与观念综合体的寄就是寻求适当的艺术形式以及这种形式与自我的关系机制,实现艺术形式与审美感受的统一,在形式的有限之中,体验艺术带来的无限。寄大致包含以下三项内容:
一,人生当有所寄这种观念;
二,一种倾心投入审美对象的寄的境界与状态;
三,一种与寓托意识相关、以比兴传统为代表的艺术手法:寄托。
其中“人生当有所寄”这种观念可以理解为主体通过客观对象(包括艺术形式)寻找生命承诺与自我价值印证,寻求人生的意义;而“一种倾心投入审美对象的寄的境界与状态”,则可以理解为主体在客观对象或艺术形式之中正在获得某种意义、承诺或印证。此观念的产生也是六朝,沈约《七贤论》中所云的“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托”是较早较明确的总结。最著名的引申说明当属明代袁中郎,他在《与李子髯》一书中说:“髯公近日作诗否?若不作诗,何以过活这寂寞日子也?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故有以奕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有以文为寄。古之达人,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景。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这便是一座活地狱。更说什么铁床铜柱刀山剑树也?”袁小修在《砚北楼记》中也附和其兄:“寂处一室,又未能即寒灰古木之事,势不能无所寄,以悦此生。”人生未能超凡入圣,未能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在寂寞枯燥无聊烦冗的日子里,要取得生命的情趣,摆脱终日忙碌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的苦恼,最佳的方法就是在理会情当有所寄的基础上,寻觅寄情的方式,投入寄情的客观世界,在文学艺术在山水朋友当中,抚慰多情多忧的心灵。
寄是一个沟通士大夫庸常人生与艺术人生的津梁,它是如何演化生成的,寄的审美特征是什么,寄与假物是什么关系,兴寄和遣寄的区别,寄与清代词学之中的“寄托”说的关系、寄与古代文论的核心观念“天人合一”、“意境”以及中国哲学“气”论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开掘出了古代文论思想、美学研究之中的众多研究课题。
2,无用。自魏晋文学自觉以后,文学——尤其诗,获得了一种在后世文学主流中居重要地位的品格,这就是遣兴娱情。这种特征是以对传统之“文学记忆”的改写为前提的,其标志就是“无用”意识的确立。无用不是一个完型的、独立的、自然的范畴,而是“无”和“用”这个观念的共同组合,它表示的是对传统之“用”——尤其有意的教化以及传统之功用的疏离,而不是对文学效用的否定。这个区分至为重要,它是保证由无用而推导出文学之美但又不沦入文学及文学研究无作用这一悲观论调的重要前提。
这里所论之“无用” ,作为意识、观念在6世纪以前有其演变过程;作为一种具有美学意义的观念,它是对康德相关美学思想的概括。康德认为:“惟有对美的鉴赏的愉悦才是一种无利害的和自由的愉悦。”[8]所谓无利害,即是了不关心的,与功用脱离的无用观。他又说,构成鉴赏判断的规定根据的,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而只有对象表面的不带任何目的的主观合目的性。此合目的性,依笔者的理解,即是最终存在的合理性与客观实在性,它仅作为一种情感形式呈现,作为一个结果,它除了具备这个结果的依据外,并不以期待这个结果的出现为目的和追求。因而是不讲利害的,是无用的。
从先秦到东汉末期,有用和无用一直处于对立纠缠中,但这个过程里,无用始终是以具体的形态被表现(如言谈的华饰、衣食宫室的奢侈等),作为被批判的对象而存在的,《墨子》、《韩非子》、《潜夫论》中都有相关的论述。比较早的从哲学上对其进行探讨的,先是《老子》、《庄子》,二人侧重从哲学范畴“无”上立论,对无用从哲学上给予了肯定;晋代葛洪《抱朴子·遐览篇》中云:“或曰,鄙人面墙,拘系儒教,独知有五经三史百氏之言,及浮华之诗赋,无益之短文,尽思守此,既有年矣。”以浮华诗文为“无益”。范晔《后汉书·方术传论》论后汉方术云:“然而后进希之以成名,世主礼之以得众,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则其有用或归于无用矣。何以言之?夫焕乎文章,时或乖用;本乎礼乐,适末或疏。及其陶缙绅,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岂非道邈用表,乖之数迹乎?”将无用已哲学抽象化,已与藻心性等美学功能相关,对无用给予了肯定,对无用之所以为用的路径作了表述:焕乎文章,时或乖用,甚至可能表面上看来与礼乐也很遥远,但其陶冶心性情趣的功能却在政教礼乐之外卓而挺出。这种陶冶“由之而不知”,如春雨润物,潜移默化。这种功能虽不是政教礼乐之用,但却是化育天下的文明之路。这样玄远之用的获得,源于玄学的熏陶与洗礼,所谓“道邈用表,乖之数迹”,正是虽假有而达无,但从有至于无的过程仍然无迹可寻。而其所推崇的在一般之用外的邈远之用,也就是玄学最终境界的体现。也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文学之中反世用的风貌得到了确立,这和一般意义的文学之自觉也基本处在一个时代。
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文学的无用观与文人的闲情娱乐消遣融为了一体,正如萧统《文选序》所云文学:“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文学乃入耳之娱、悦目之玩的对象,是闲暇中的寄托,是与世用了不相关的无用,也正因为如此,其对文学的评价标准才定位在“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可见无用这个范畴是实现传统的文学教化向文学审美进化的核心范畴,此前尚无明确的归纳与翔实的研究,如无用作为一种文艺观美学观的发展演化历程、文人们在充满美学意味的活动里如何开拓显示无用,或者说无用是以什么独特的途径进入文人闲情的范式或寄托的手段、与无用相对的用在历史上经过了怎样的变异或丰富、无用和用之间在历代协调的途径与获得的效果、无用观在文学创作上具体的体现标准、如何理解汉代文学重视“文加学”而魏晋之后文学创作强调“才”的现象以及对“才”的解读等等;由此衍生出的理论话题又如道艺论的产生以及表现,唐柳冕《答荆南裴尚书书》中首标这个问题,道和艺在文和志、言和行、致用与求趣味重形式之间展开,其彼此消长的过程里提示了文学之艺与道疏离的轨迹,其原因与闲情观念相关。
其它研究范畴又如因闲情审美而出现的古代文论对境界与风格描绘的“闲”,由对闲的崇尚诞生的《文心雕龙》之中作为文机涵育的“入兴贵闲”、“弄闲于才锋”以及《南齐书·文学传论》中的“启心闲绎”,这都是基于“养气”的需要才提出,成为可涵盖人生境界之滋育和艺术创造之心境的一体化理论体系。再如遣性娱情之“娱情”,江淹《自序》“放浪之际,颇著文章自娱”,钟嵘《诗品序》“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者,莫尚于诗矣”等等,皆就诗文能排遣抑郁、陶冶性情而言。昭明则直以文为“入耳之娱”,“悦目之玩”④。以文致逸,以文娱情畅性,为而不劳,顺性而为。由此衍生出的话题是,娱情之说和早期的言志说是什么关系?娱情说的产生对文学题材与体裁有什么样的开拓?历代都不乏苦吟诗人,苦吟是否与这种娱情观对立?苦吟的审美意义在哪里?等等。其它如笔者曾经专门探讨的“赏”,与闲情相对立的“累”等等,都与文人的生命状态相关,是了解中国文人心灵的重要范畴⑤。
闲情与文学的研究,自然不仅仅局限于笔者所论,以上只是就笔者已有的研究心得作的一个初步梳理,是一个起例发凡的纲目。由于这个观念对中国古代文人深入持久的影响,二者之间可以说还有着众多的研究课题,其研究不仅仅对开拓我们的文学研究有益,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深化我们的文学研究,并使文学研究更进一步地回归到“人”。
①“赏际奇至”出于《文心雕龙·诠赋》,是刘勰所批判的当时的一种创作风尚,而这正说明其在当时的流行,详细辨正请参阅拙文《从“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的偏颇看刘勰文艺思想的保守成分》,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②关于“寄”这一审美范畴,请参阅笔者与詹福瑞师合作的文章《论寄的审美特征——对一个古典美学重要范畴的文化考察》,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
③笔者在博士论文《闲意悠长:中国文人闲情审美观念演生史稿》(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10月出版)中曾对“闲情文学”做过初步交代,徐公持先生在评议书中认为,这是“一理论性宏观性较强的课题,前人研究不多,近年有论者稍有涉足,而未形成系统,论文正面提出‘闲情审美观’及‘闲情文学’予以讨论,具有开拓意义和前沿性”。
④关于“娱情”说,可参阅笔者与詹福瑞师合作的文章《从志思蓄愤到遣兴娱情——论六朝时期的文学娱情观》,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⑤其中的“赏”和“累”笔者都曾做过初步的探讨,参阅拙文《从六朝文人对“赏”的审美认知看〈诗品序〉“赏究天人”之不误——兼论六朝之际“赏”这一美学范畴的确立》,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6期;《累之义与累之叹》,甘肃社会,2004年第3期。
:
[1]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96,第1220页。
[2]王瑶:《读陶随录·闲情赋》,《王瑶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
[3]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98。
[4]冯友兰:《论风流》,《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5]袁济喜:《六朝美学》(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6]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第三章《建安诗歌》,河北出版社,1997。
[7]罗庸:《笳吹弦颂传薪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311页。
[8]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4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