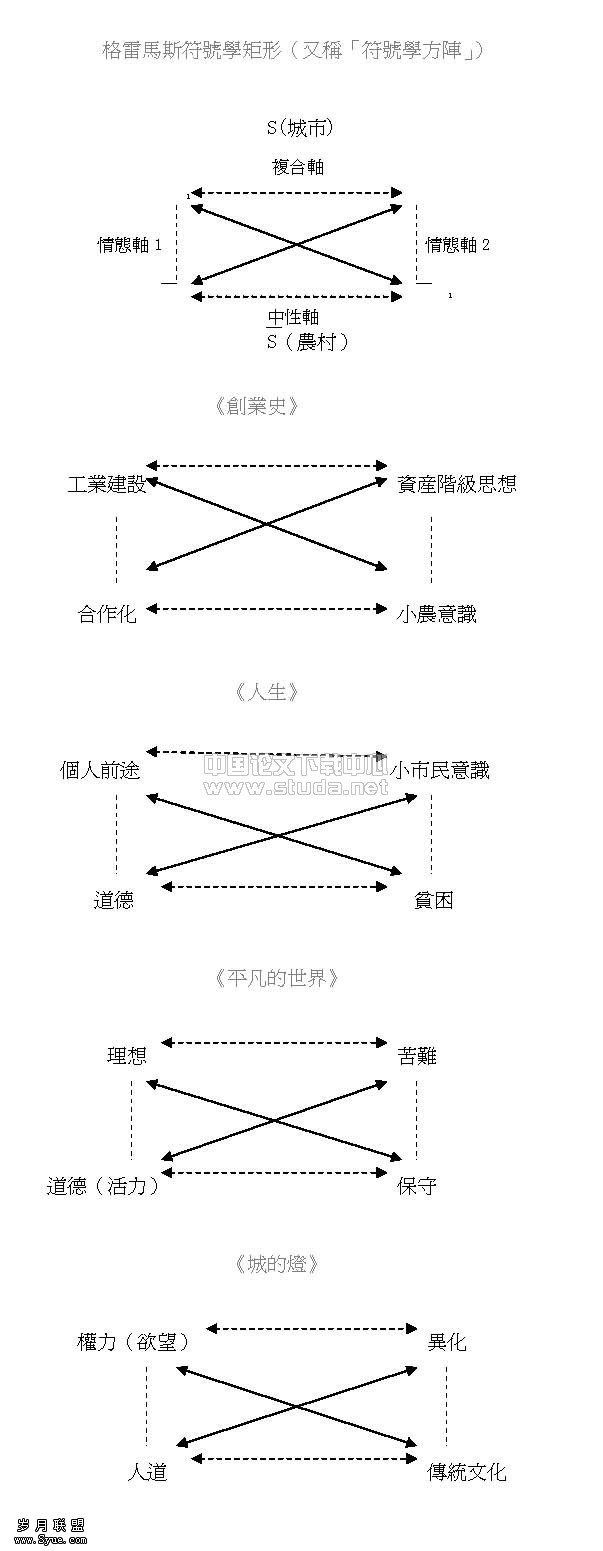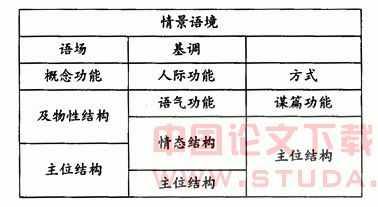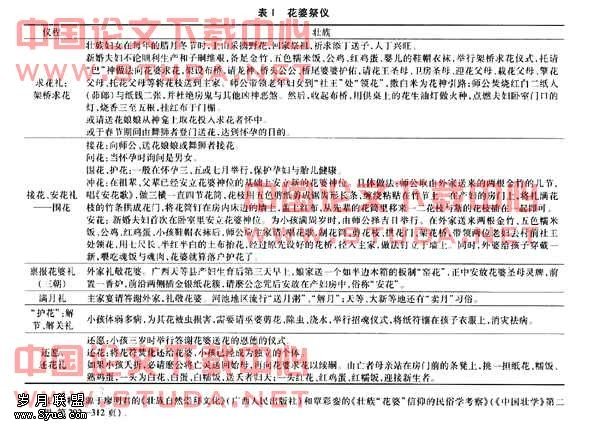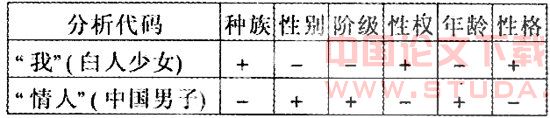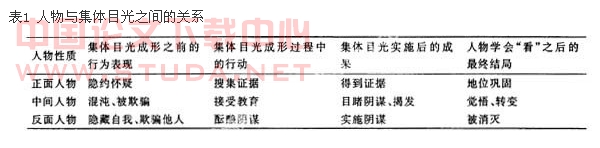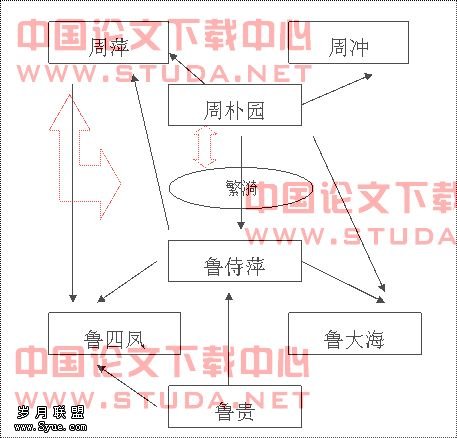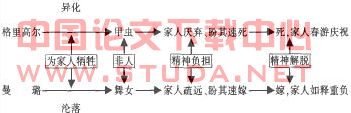地域文化视野中的左翼话语——浙东左翼作家群论
【内容提要】
浙东左翼作家群是30年代左翼文学中一个最庞大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群体,其形成取决于独特的地域背景和诸种文化的合力。这个群体所提供的左翼文本,显示出体现浙东风尚的地域“乡野风”特色,而许多作家在创作中的独特话语方式拓宽和丰富了左翼文学内涵,提升了左翼文学品位,对其作整合研究,对于左翼文学创作的经验不无裨益。
研究左翼文学会发现,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来源的地域分布,既呈全国铺展态势,又有相对集中的区域。据姚辛编著的《左联词典》“左联盟员简介”①,在总数288位盟员中,按省籍统计,位居前五的是浙江(47人)、江苏(31人)、广东(31人)、湖南(19人)、四川(17人)五省,共145人,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反映了左翼文学风潮在特定地域内的强势显现,它势必给予整体的左翼文学以特殊的影响力。此种左翼作家来自相对集中的区域,从而形成左翼创作的独特地域风尚现象,也曾为研究者所注意。杨义在《中国小说史》中论述左翼文学,就特别提到“左翼文坛的乡野风”,论述对象便是走出左翼作家甚众的浙江、湖南两省,并以“浙东曹娥江的忧郁”和“湖南洞庭湖的悲愤”为题,分别论述了这两地作家的不同创作风貌②。可见从地域文化视角研究左翼作家群体,从中透视左翼文学的某些性特点,应该是饶有兴味的话题。本文论述的浙东左翼作家群,便是左翼文学队伍中最有影响的一个群体,透过这个群体的构成及其创作文本的左翼话语呈示,当能窥见左翼文学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一群体形成:地域背景与文化合力浙东左翼作家群在左翼文学队伍中的强势凸现,的确呈现一种夺目景观。这个从浙江走出的作家群体影响之大、地位之显要,不仅在于阵容壮观(其出场人数之众居于各省绝对领先优势),更在于其引领左翼的地位:鲁迅、茅盾历来被视为左翼文坛的“盟主”,甚至连当时的国民党报刊都惊呼他们是左翼的“两大台柱”③;还有两位浙江作家冯雪峰、夏衍,既是“左联”的发起人,又长期担任“左联”的实际组织工作;类似的浙江左翼作家如朱镜我、楼适夷、王任叔(巴人)、徐懋庸、艾青、沈西苓、陈企霞、魏金枝、何家槐、黄源、林淡秋等,都是任何一部中国新文学史都不能不提及的“左联”作家名字;其中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也以浙江作家为多,较著者就有柔石、殷夫、潘漠华、应修人等著名“左联”烈士,他们彪炳于世的功绩更令后人敬仰。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汇聚一支如此壮观的左翼队伍,足够令人惊叹,而透过其所由构成的诸种复杂因素,则可以在独特的文化聚合背后看出左翼文学的存在特点及其深在意义。从表层看,这个群体的形成同20年代后期新文学中心南移不无关联:浙江与“左翼”中心上海临近的地域亲缘关系,促成浙江作家由“边缘”向“中心”位移,为更多作家介入左翼提供了机遇。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中心在北京,浙江作家的介入,总有地理上的阻隔,不免有许多局限,如颇有声势的“五四”乡土文学创作,就难于改变如鲁迅所说的“侨寓文学”④的性质;那么,到了这一时期,文学中心就在邻近,必然会带动一大批浙江作家走进上海的文学圈子,在创作上也会更有所作为。事实上,此种状况不独以浙江为然,江苏的左翼作家数量位居第二,乃至广东、湖南、四川各省也呈左翼甚炽之势,同样联系着地域因素,而且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反映了中国30年代因左翼文艺运动的展开作家队伍新格局的建构。
中国的30年代文学,是因以上海为中心蓬勃展开的左翼文艺运动而日渐壮大其声势的。由此,中国新文学发生又一次历史性变革: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到30年代的“革命文学”的转化。此种转化,造成中国新文学的一次大规模的空间传动,即新文学中心南移和南方地区作家队伍的拓展。“五四”落潮以后,“苦闷彷徨的空气支配了整个文坛”⑤,而以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方为尤甚。曾是“五四”新文学策源地的北京,此时也显得死气沉沉。鲁迅描述的“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⑥,是对此的生动写照。富有变革精神的新文学作家,当然难耐此种寂寞的气氛,便纷纷南下当时革命空气高涨的广州、上海。而当大革命失败,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时机成熟,遂有一大批作家汇聚上海,成立“左联”,掀起声势浩大的左翼文艺运动。如此态势,对于促成新文学作家队伍结构的调整与外延的拓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以鲁迅领衔的浙江左翼作家群的形成;当是典型例证。地域亲缘关系容易使鲁迅同前进的浙江文学青年心灵沟通,而鲁迅的召唤也的确给浙江新文学作家队伍的重新组建和进一步充实产生重要影响。鲁迅到上海不久,即与郁达夫联手创办《奔流》杂志,介绍革命文艺理论和作品,这对郁达夫最初一度加入“左联”,无疑有显著影响。鲁迅对来自宁海的青年作家柔石,立即给予了信任,与之合办朝花社,编辑《语丝》,使其得到锻炼,后来又一起发起成立“左联”。他同冯雪峰保持着长期的友谊与联系,这位来自浙东的质朴而耿直的青年显然与他灵犀相通,在彼此的亲密合作中推进了左翼事业,冯雪峰就成了他与共产党沟通的最重要的桥梁。此外,夏衍、殷夫、楼适夷、徐懋庸等等,一个个都是在他的扶掖、指导下成长为坚强的左翼文艺战士,且在后来的文学活动中有更长足进展。从这一点看,左翼文艺运动作为30年代“唯一的文艺运动”⑦,它对于中国新文学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展开的确有着无可漠视的意义,单就新文学队伍建设而言,其意义就是远远超越于文学自身的。
考察浙江左翼作家群所出自的地域,除一两个作家是从浙西走出的外,绝大多数来自大革命时期革命气氛高涨的浙东,尤以浙东的宁波、台州两地为甚。这里显示的是群体形成的另一个原因:即与浓厚革命情势的遇合是作家走向左翼的重要驱动力,从中反映出左翼文学作为“文化”形态显现的存在意义。“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念和感情。”⑧左翼文学所由产生,与特定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心态密切相关。30年代的时代语境是民众的政治热情普遍高扬,人们对专制制度的失望一变而为改革旧制度的共同心理期待,因而关注社会变革的风气特别浓厚,而左翼作家是“用被压迫者的语言”来“抗议和拒绝社会”⑨,他们以“被压迫者”的姿态反映强烈的政治制度变革要求,实际上是以民众参与意识显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就必然会引起社会的普遍心理共鸣。文学与一个时期流行的政治态度、信念和感情紧密一致,以切合民众心理、民族需求为前提,才能使其获得最大的接受可能和最广泛的文学创作趋求,从而使一个地区的作家集结于同一文学领域成为可能,也会召唤更多的作家加入左翼文艺队伍。中国左翼作家走出特多的区域,往往联系着该地蓬勃高涨的革命情势和民众的普遍热情,如农民运动开展得最为热烈的湖南和曾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这既是革命的情势使然,也由此内化为作家的一种自觉心理诉求。浙江的情况也大体类似。虽说其时浙江全境的革命运动不及两湖、广东等地高涨,但正如当时的中共浙江省委所分析的:“浙江农民并不因浙江的富庶而革命性弱,反因富庶而被剥削更苦”,因而,农民“推翻封建势力亦愈迫切,土地革命适为浙江农民目前斗争之中心问题”,特别以浙东地区“为甚”⑩。大革命失败后浙东相继爆发的奉化暴动、三北暴动、宁海亭旁暴动等,曾在浙江大地上掀起波澜,这是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倾向革命、走向左翼的一个重要背景。后来走向左翼的浙东作家巴人、朱镜我、楼适夷、柔石、许杰等,正是在亲历或感受了这里的革命声浪以后才确立新的文学意向,立志要用更切近时代心理的文学来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这当中,柔石走向左翼最具典型性。他原在故乡宁海中学任教,一度担任县局长,立志“开展宁地之文化”,政治态度属“中间偏左”,“同情共产党”11:宁海亭旁暴动失败后,曾为暴动指挥中心的宁海中学被蹂躏,他深感教育无望、理想毁灭,更痛恨反动当局镇压革命之凶残,才愤然离乡去沪,投身左翼文艺运动12。时代的呼唤成为作家转型的无形感召力,顺应文学潮流促成许多作家加盟左翼,甚至不惜以身相殉,即此而言,左翼作家及其创造的左翼文学自有其独特价值,实在不可以等闲视之。
从地域文化考量,浙东左翼作家群的形成,还有更深层动因:应该同此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不无关联。一个饶有兴味的事实是,鲁迅引领的“五四”浙东乡土作家群同仍由其领衔的浙东左翼作家群,不独有着地缘上的关联,同时也有群体组成上的叠合:上一期的乡土作家如许杰、巴人、潘训(漠华)、魏金枝等,此时大都成为左翼作家。这不是偶然的巧合。正同乡土作家群只会产生在浙东,不可能出现在浙西,左翼作家大多集结于浙东,不大可能出现在浙西,这除了革命情势的条件外,地域文化精神的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地域文化积淀联系着一个地区的民情、民风,也同作家的精神品格、个性气质的养成产生潜在影响。浙东“越文化”刚性精神的传承,与浙西“吴文化”柔美品格的延续,导致两地截然不同的文风,这在新文学中也有例可证。“吴文化”是产生柔美文学的土壤(鸳鸯蝴蝶派就在此聚集),多情浪漫的作家如徐志摹、郁达夫、戴望舒等也大多出于此。而“越文化”的刚性质素则造就作家的坚硬品性,走出诸如颇具浙东“台州人硬气”的柔石、许杰这样的作家,是故就有坚硬劲直的乡土文学和左翼文学。即便就左翼文学产生的显在因素——革命性而言,也联系着一个地域的民性、民气。鲁迅指出过的“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与湖南山岳地带之民气相同”13,恰恰暗合了大革命时期类似于湖南地域的浙东民气高扬的特点。在这样的地域文化环境中,孕育出具有现代特质的刚性素质作家,恐怕也是一种必然性现象。当然,关键在于时代条件的成熟,一旦置身在革命声浪高涨的时代环境中,作家的刚性素质就有可能向着革命方向转化。浙东作家中有一部分是在“五四”落潮以后的感伤时代里开始文学创作的,其时他们既有积闷要吐露,又感觉着前路茫茫,创作难免呈现出一种低色调。当新的时代思潮来临,意识到个人解放要求必须同社会解放融合在一起时,他们必会眼睛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迅速完成创作倾向的转变。殷夫从早期《孩儿塔》里唱出无爱的忧伤到投身大众唱出无产阶级的战歌,柔石从哀叹“旧时代之死”到注目劳苦大众,都没有经历太久的时间,由此昭示着:地域文化精神所产生的潜在力量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作家创作精神、风格的形成与转化。
二 浙东风尚:左翼文学“乡野”风
左翼文学就其发展大势看,它反映了整个30年代社会的历史变动,在文学表现现实革命斗争重大题材、反映人们变革旧社会、旧制度的普遍渴望方面显示出整体一致性。然而,由于不同地域革命斗争的形势并不完全相同,作家看取左翼文学的视角也有差异,这就有可能形成各地左翼文学不同的创作风貌、创作个性,遂有显示地方色彩的左翼文学“乡野”风的涌现。而此种“乡野”风的形成与汇聚,在一定意义上是克服左翼文学初期创作弊端使之渐趋成熟的一个标志。如果说,初期左翼创作之病是在于凌空御虚,作家毫无生活实感,又急忙制作大而无当的革命三部曲,仅以浪漫蒂克幻想布置一个又一个“革命方程式”,描写一个又一个“脸谱主义”人物14,势必受到人们诟病;那么,“乡野”风的形成无疑为左翼文坛吹来一股新风,它以质朴、清新的生活描写使左翼创作真正落到了“实”处,同时也因各地“乡野”风的共生竞存,有可能使左翼文学作品在审视社会、表现革命、传达左翼话语方面显露出斑斓色彩,从而使左翼创作开出一种新生面。
浙东左翼作家群作为左翼的一个最重要创作群体,其创作上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基于这个群体生成的地域背景及作家观照生活的独特视角,其创作价值突出地反映在左翼话语的地域文化个性呈示,即在着力表现体现浙东风尚的地域“乡野”风方面显示出自己的特色。这一视角的选择,既有作家创作上的心理习惯因素,但首先取决于作家在特定地域背景中的感受与体验。例如,左翼文学曾一度流行写“尖端题材”,要求表现两大阶级的生死对抗与激烈冲突。由于经历所限,这就非浙江作家所长。在浙江地域上曾发生过自发的或有组织的小规模革命暴动,但没有产生类似于江西、湖南那样牵动全国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和暴风骤雨式的农民运动,因此,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描写,如叶紫的《丰收》、《火》等作品那样直写声势壮阔的湖南农民运动,乃至号召人们上“金钢山”(井岗山),就不可能出现在浙江作家笔下。虽然为突进“时代的核心”,浙东左翼作家也为此作过努力,一些作家着眼于沿海地域的革命斗争描写,如楼适夷的《盐场》写浙东余姚一带的盐民暴动,巴人的《六横岛》写舟山群岛中一个小岛的渔民暴动,提供了一般左翼创作很少见到的斗争画面,不妨说也是丰富了左翼文学在这一题材领域里的表现。但终究由于表现视角太小,对“革命”刻划不深,这类作品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对浙江作家来说,扬长避短,找到一个适合于自己的表现视角,以期对促进左翼创作的深化有所贡献,应该是明智的选择。这样,奋力于向“乡野”掘进,便成为他们最为可取的视角,由此也显示其创作的一种特色、一种优势。
注目“乡野”,依恋乡土,表现乡土,曾是浙东作家在“五四文学”时期就开创的创作风气。来自浙东的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冯雪峰曾在其诗作《雨后的蚯蚓》里写道:“蚯蚓们穿着沙衣不惜地扭动”。另一位浙东作家潘训(漠华)也曾写过一首《雨后的蚯蚓》:“雨后蚯蚓般的蠕动,是我生底调子”。如果用“穿着沙衣的蚯蚓”这样的意象来比拟浙东作家的“生命基调”是最贴切不过的。对这种钻进泥土深层、与土地共同着生命的生灵的礼赞,恰恰是浙东作家情系地母、依恋乡土的真切写照。进入30年代,浙东作家大多转化为左翼作家,他们曾倾心表现过的乡土,当然依旧为他们所关注、所瞩目,而面对落后面貌依旧,而且变得更坏的乡土,他们自会投入更注视的目光。由是,透过浙东这块颇具地域个性的“乡野”在30年代时代风潮中的剧烈动荡和变迁,去把握那个时代的特质,就成为浙东左翼作家的一种重要选择,创作也因此呈现出承续五四、超越五四的特点。表现乡土的作品,在“五四文学”层面上,大抵停留在对古老乡土文化的审视,作家们致力于乡村群落人们的落后国民性探讨,从历史形成的精神蒙昧角度寻求农民思想落后人性麻木的根源,这几乎成了那时期乡土小说的一个根本性主题。到了30年代,社会现实是风云激荡,沉滞的乡村也在剧烈动荡中,乡民们在努力走出愚昧、走向坚实,作家们就会用另一副笔墨去看取乡土、表现乡土。魏金枝曾被称为“中国最成功的一个农民作家”,这不免过誉,但说这位来自曹娥江上游的农家子弟,“以忧郁的含泪的文笔,写出了古旧的在衰老,在灭亡,在跨进历史的坟墓里去,这情调,凡是作者的无论哪一篇创作里都弥漫着的”,却是的论。其创作从“五四”到“30年代”,就实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跨越。他的早期乡土小说《留下镇上的黄昏》写小镇上无聊的“看客”无所事事,只围观小贩宰杀黄鳝,是对一种国民精神的观照,小说阴冷、滞重的氛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色调。成为左翼作家后,魏金枝尽力用革命视角透视乡土,一面埋葬着毫无生气的“古旧的农村”,一面提示着乡民新的生路。三万余言的《坟亲》写一个看守公坟的诚实农民的苦难一生,其阅尽人间沧桑的确昭示着衰败农村应“跨进历史的坟墓里去”,而主人公顽强的生存意志则展示了农民倔强、坚韧的品格。《奶妈》写充作“奶妈”的农妇,从一个普通农妇成长为秘密的女革命者,很长时间被人怀疑行为不端,并有“告发者”之嫌,最后真实身份暴露,英勇地牺牲在敌人屠刀下。这篇小说在当时的革命小说中实属翘楚,除了技巧上的精心结撰外,还有对时代风云激荡下妇女、乡民心理的深层透视。《白旗手》写士兵哗变:一群新兵不堪受辱,在白旗手——一名勤务兵的组织下联合“乌合的难民”揭竿而起,走向新的反抗道路,探索着农民的生路,显示出更浓厚的革命色彩。另一位乡土小说作家巴人(王任叔),有着更丰富的革命经历,大革命前后一直处在革命斗争旋涡中心,但其创作也经历了基调的转换:早期作品写农民被生活“压弯了脊骨”,欲“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而不得(《疲惫者》);到了30年代写出的《乡长先生》,乡民们喊出了“要干就要干个硬朗明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用性命来换饭吃,倒也显得做人一分骨气”,透出一股血性硬气,同样烙刻着时代风云的印记,显示出创作与时代俱进的趋向。有的作家并没有直写乡民革命,但却在刻绘乡土的时代苦难上见出深度。创作起步于30年代、在40年代颇负盛名的浙东左翼作家王西彦,也以乡土小说驰名,他同样写着悲凉乡土上的坚韧人性。其状写浙东悲凉乡土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承续着鲁迅和许钦文、王鲁彦们开创的主题,其表现乡村的愚昧和落后国民性的沉重,不难在两者之间找到联系。只不过身处“更坏”的时代里,王西彦会以更沉郁的笔调去营造悲凉的乡土氛围。他是以更冷峻的眼光观照着30年代黄土地下的紫色灵魂,其状写的死难图画简直是对燥裂大地上的死亡的写生。土性的思维在浙东作家那里是一脉相承的,从后起乡土作家创作中可以窥见他们对前辈作家创作精神的承传,他们共同的艺术追求几乎就是一种时代的接力。
作为左翼话语的地域文化个性呈示的,还有浙东作家在把握独特时代风尚中透出的鲜明特色,这便是依据浙东的社会状况,从经济文化视角切入,用力表现农村经济崩溃所产生的社会深层次矛盾,使作品在反映、剖析30年代的时代特质上见出优势。有论者指出,在30年代左翼文学中,“写旧农村经济崩溃的作品比写农民暴动和苏区斗争的作品取得更为巨大的成功”15,此语不虚。30年代的时代特点是阶级矛盾加剧、社会动荡不安,导致城乡经济崩坏、人民日益陷于贫困。这样的现实状况因其带有普遍性,是远比不断鼓吹“暴动”之类题材更应引起作家关注的。正缘于此,“左联”在以往创作的教训以后,于1931年作出关于题材问题的决议,要求作家必须面对现实,抛弃以往那种只写“革命的兴奋和幻灭”、“恋爱和革命的冲突”之类“定型”题材,应密切关注“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广大的题材”,尤其把揭示“农村经济的动摇和变化”等作为重要内容来表现16。这一要求就纠正初期创作偏向、促进左翼文学深化而言,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事实也证明,作家们克服浮躁情绪,把笔触伸向生活深层,努力表现农村经济破产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创作就取得长足进展。这当中,浙东左翼作家基于该地农村经济破产问题的鲜明性与尖锐性,予以重墨描写,显示出他们在把握时代主题方面的敏锐感知力和深沉表现力,在整个左翼文坛都产生重大影响。浙江的富庶原是其作为沿海省份的重要经济特征,然而在30年代的特定时代环境中,这里的农民“反因富庶而被剥削更苦”,连年遭受灾荒、饥饿的煎熬,这就使经济破产的时代问题变得更为尖锐、突出,作家们去用力捕捉和表现这一话题,这对于深入透视那个动荡时代的本质应当更具表现力。在这方面,左翼小说的领衔者茅盾的创作,为浙东左翼作家作出了表率。茅盾的小说从一个重要视角——经济视角,描写了从城市到乡村、从到农业的经济全面崩溃,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遍性矛盾,而这一矛盾的揭露,是通过富庶的江南农村经济的崩溃来表现而增加了透视力。其作品的背景以杭嘉湖为中心辐射上海的地域特色,反映了30年代浙江乃至江南社会的深刻变动:原本衣食有余的自耕农(如老通宝)此时已走上破产之途,经营有道的小商人(如林老板)也面临商铺“倒闭”的命运,而当铺前的门庭若市(《当铺前》)则更昭示出经济的畸形繁荣;作品中出现的买卖洋货、横冲直撞的小火轮等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折射出那个时代典型的沿海地域特点,对城乡经济破产的社会根源作了有力的揭示。毫无疑问,在30年代表现经济破产的创作中,茅盾的思考是最见深度与力度的。这固然得益于作家深厚的积累,也同他善于在一个富有表现力的题材领域里的深入开掘不无关联。茅盾创作的成功,及其创作视角的选择和作品显露的鲜明浙江色彩,对浙东左翼作家是一种鼓舞,也是一种无形的感召,青年作家巴人、林淡秋等,取材于浙东农村,注目于经济领域,写出社会的剧烈动荡在农民心里投下的深重阴影以及农民在经济恐慌面前的极度贫困,一度构成浙东左翼文学一种颇见声势的创作风气。林淡秋的《散荒》写原本并不贫困的小村也无端遭荒,以至于农民年关将近尚衣食无着,不得不祈求当局“散荒”(赈济),然而饥寒交迫的乡民被愚弄一番以后,并没有得到“布施”,依然饥肠辘辘,这终于使得领到过几升米的乡民愤然将米倒进街边的污沟里,锋芒直指经济制度。巴人这时候也将创作视角转换到农村经济题材,写出《灾》、《牛市》、《佳讯》等一系列作品,表现动荡时代的农村经济状况,揭示农民贫困的社会根源,与茅盾小说的社会剖析有着类似的思考。《灾》描写“精明”的地主比他的祖辈更“棋高一着”,他不再满足于“总是把从土地上赚来的钱放在土地里”的敛财办法,而是土地以外,又通过办钱庄、开商行等手段向农民盘剥,终于使得农民灾祸丛集,不堪其苦;《牛市》写经济凋敝,牛市不兴,技艺精湛的屠夫已无事可做;《佳讯》写租、债、捐、税的层层剥削,农民已是负债种田,土地失去意义,即使把田送人也没有人要。这些作品反映了当时经济的一个“死结”;社会政治的腐败必促成社会经济的全面崩坏,农村的破败必在所难免,即使再富庶的地域也不可幸免,从而有力地表现了那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无可挽回的颓势。切入特定题材领域,表现鲜明时代主题:这种不可取代的特色,既有浙江人创作左翼文学的标记,也必以作品鲜明的地域色调造成浙东作家创作在左翼文学中的优势。
三 深层拓展:提升左翼文学品位
论及左翼文学创作成就,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尽管左翼文学理论的政治意识、阶级意识日趋强化,但左翼创作仍有着丰富的形态,内中不乏创作高手与艺术佳构,因此,笼统地把左翼文学看成仅仅是泛政治化文学,艺术品位不高,是不恰当的,至少是不够全面的。因为在左翼文学时期,理论的喧闹与创作的展开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左翼作家的创作仍有相当的自由度,并不完全是在一个先定、封闭的文学规范和整齐、划一的文学框架内运行,每一个作家个体的创作便会呈现出复杂状况。而且,多数左翼作家都是从“五四”走来,“五四”孕育的追求民主自由、融通各种思潮的艺术精神到左翼时期不可能就截然中断,因而在30年代左翼文学中,以反封建为核心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思潮依然得到张扬,只是反封建的内涵带有更多的现实印记,仍会有作家继续探索“人学”命题,并使其在深层开掘中有所深化。鲁迅是最典型的例证。其创作的主导倾向是强化了阶级意识,但无论是杂文还是小说(《故事新编》)创作,都仍有对中国“国民性”弱点的深刻剥露,有对封建文化和封建
意识形态的犀利批判,表现出承续“五四文学”主题的鲜明意向。浙东左翼作家群的创作,就整体而言也可作如是观:他们顺应革命文学潮流,大都表现出走向革命的倾向,但由于这个群体在一个独特的文化环境中生成,有着自己的独特审美价值取向,且作家的创作多起步于“五四”,便有对“五四文学”的深情眷顾,其创作必会显出超越左翼的泛政治化走势,从而为拓宽左翼文学视野、丰富左翼文学内涵,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从审美视角看,浙东左翼“乡野风”所呈示的创作基调是“忧郁”,颇不同于“湖南风”的“激愤”,显示出独特的艺术审美效应。“忧郁”基调在魏金枝、潘漠华、林淡秋等的小说,艾青、殷夫等的诗作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其与“湖南风”的差异,既源于两地不同革命斗争情势下作家所产生的不同情绪感受,同时也来自作家出于不同地域所产生的文化心理感应:“激愤”往往是面对即时爆发的现实残酷性的强烈反弹,于是就有激越的反抗声浪;“忧郁”是对渐滋渐长而又沉淀太多的痛苦驱之不去的伤感,其背后潜藏着的往往是对积淀深厚的病象、病痛的忧虑,并非眼前激烈斗争的即时反映。艾青曾有对无边的黑暗和苦难地母的呼唤,并将此作为他艺术思维中幽深神秘的动力源:“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为爱土地而落泪,显然是“土地”承载了太多的苦难,这苦难无际无涯,超越时空而存在,于是就有无边的忧伤。“忧郁”是艾青诗作的基调,其“忧郁”之所指,就既包括眼前身受或目睹人民苦难的心理感应,也蕴涵诗人更广泛的情绪感受,是一个扩大了的情绪能指范畴,包含了指向人类、面向过去与未来的超越特定时代性和阶级性的丰富内涵。恰如艾青所说:“把忧郁与悲哀,看成一种力!把弥漫在广大土地上的渴望、不平、愤懑……集合拢来,浓密如乌云,沉重地移行在地面上”17,这就使其诗作有更开阔的胸襟和浑厚的力量。其成为左翼作家后被投入监狱创作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便是一首使“忧郁”情绪得到艺术升华的著名左翼诗作。此诗洋溢着泥土气息,有大量富有浙东风情文化色彩的农村生活事象描写,显出十足的“土”味,昭示着这位从浙东土地上走出不久的诗人对故土的眷恋,对土地的挚爱。诗作生发出诗人对“土地”的无限感兴:既有一位“地主的儿子”转变阶级立场对一位无私奉献一切的普通农妇——“土地”母亲的礼赞,显示出诗人明确的左翼立场;诗作同时表明此诗也“呈给黄土下紫色的灵魂”、“呈给大地上一切的”受难者,是对人间一切苦难的审视,其间包含对人的生存命运的莫测不安,越出了单一“阶级压迫”层面,故而能引起各阶层人们广泛的心理共鸣。艾青诗的力量就在于,深层开掘诗作内涵,立足左翼又超越左翼,这无疑是对左翼文学艺术品位的有力提升。另一位浙东左翼诗人殷夫的诗作,在左翼诗中也有不俗的品位。鲁迅称殷夫的诗“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18,是就诗作蕴涵丰富的情感内涵作出的评价,可谓独具只眼。其早期诗作《孩儿塔》的基调是伤感,那诉说个人心灵痛苦的低回婉转,感人至深;即使后来直写革命的诗篇,也不乏丰富情感渗透。其一曲《别了,哥哥》,强烈的政治抒情内涵和婉转的兄弟情谊抒写相融合,表达一个革命者的磊落情怀,曾使许多革命者为之动容,也令普通读者心灵震撼。这一类诗作有着远比“战叫”更动人的力量,它们是左翼文学创作中更值得珍视的精品。
浙东左翼作家群的创作对左翼文学的深化,还表现在从地域文化视角切入,透过凝重、沉郁的笔调表现乡村的落后性及其亟待改造的一面,从而使创作显示出超越于社会批判的深刻文化批判意义。就整体而言,浙东作家当然也涉及现实社会批判,但很少描写“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内”的人物和生活,大多避开了刀光剑影的重墨渲染,更多关注的是乡村日常生活体验:农村的凋敝,荒年的煎熬,盗贼的横行,乡民的无奈,甚至于还有农村寡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痛(魏金枝《报复》),流落城市的乡民遭受无妄之灾(巴人《仿佛》)等等。这类作品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义,但更显著的是文化批判色彩。魏金枝的《报复》写一位乡村寡妇被鸦片鬼秋老板奸污生下“野种”,背负“失节”恶名,遂到尼姑庵带发修行,以求洗刷“龌龊”;不意20年后,那个长大了的“野种”竟到庵堂认母,她仍感莫名羞辱,竟在拥抱之际用利刃刺杀了“野种”,演出了亲母杀子的悲惨一幕。小说含有对社会恶势力的谴责之意,但更多的是表现封建礼教文化给妇女造成的伤痛。潘漠华《冷泉岩》对传统文化习俗的冷静观照,更似远离时代主潮。小说写
发生在离开县城五十里外的深山冷庙里的故事,这里的人们还过着半人半兽的生活,童养媳、典妻制度的流行,使女人毫无人性尊严。这纯粹是对传统习俗的批判,要不是小说借人物之口喊出对邻村“第一财主”的不平呼声,很难将其同左翼小说并举。而对“典妻”习俗、女性命运作了更深入开掘的,则是柔石的名作《为奴隶的母亲》,作品写一个沦为生育工具的“母亲”依违在两个孩子间难以割舍的情感,演绎了人间的惨剧。这一幕情感悲剧的制造者,主要也是封建文化习俗本身,而非某个恶人恶行,从而使作品浓厚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意义。以往认为这篇小说只是作家向着左翼“转换”的标记,还不是地道的左翼文学,原因也在于其批判阶级压迫的左翼色彩不彰。事实上,无论是《冷泉岩》还是《为奴隶的母亲》,从文化视角透视“乡野”落后习俗的滞重、板结,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乡村改造的紧迫性,拓宽左翼文学的表现视野,应当也是左翼作家的一项使命。风俗文化批判,曾是浙东“五四”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进入左翼文学时期,作家们依然在一个擅长表现的主题领域里掘进,而且以左翼的眼光审视30年代乡村文化毫无长进更待改造的一面,显然是对以往创作的一种超越。试看《为奴隶的母亲》一类作品至今仍为人们传颂,显示出不竭的艺术生命力,为左翼文学赢得了声誉,证明着致力于文化批判恰恰是使左翼文学艺术得以提升的一个途径。
与文化批判在同一层面展开的,是许多浙东作家突破左翼文学理论的模式化要求,创作表现出超越单纯的阶级性理念,重视对“人”以及人性的丰富、复杂性的审视,从而在延伸、拓展五四的“人学”命题上为提升左翼文学价值提供了范例。人性、人道主题的放逐,曾是左翼文学理念和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左翼作家显然强化了阶级意识,人性、人道话题已很少在左翼理论家们的口碑之中,文学创作也大抵视表现人性、人道为畏途。由是,后来的研究者也往往把是否蕴涵阶级性作为判定左翼文学属性的重要依据。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实际上,体现人性、人道倾向的创作并没有在左翼文本中绝迹,特别在一些重视文化意义揭示的创作中有更显著的呈示。这一方面是由于左翼文学理论在当时并没有成为作家必须遵循的理论规范(像后来文学体制化时期那样),作家依据自己的眼光和思考选择表现视角依然起着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左翼文学目光投射的依然是下层人民的苦难,这一目标同五四文学没有太多的相异之处,或者正可以说是对五四文学传统的一种延续,因而创作表现出承接五四“人学”主题的一面也是很的。许多作家对“苦难”的审视,就不是绝对的“阶级对立”理念,倒是大抵停留在贫富差异、善恶对立、落后的文化习俗、社会恶势力横行等因素上。因此,当他们审视人的生活与与命运时,尤重人的个性开掘,往往会从人性视角揭示人的固有弱质,探索造成这些弱质的文化、伦理、道德因素(而非阶级对立、阶级压迫原因),作品会进发出对反人性、反人道现象的激越批判声音。这在浙东作家的创作中表现非常突出。唯其许多作家对人的审视侧重于文化心理透视,于是就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对人性的撕裂,导致一个柔弱寡妇的心理变态(魏金枝《报复》);就有原本老实的农民因生活所迫沦为小偷,“在旧社会旧习俗道德”之前“低头受缚”(巴人《灵魂受伤者》)。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之所以历来烩炙人口,除了文化习俗的批判意义而外,还在于人物深层心理开掘中所显示的人性深度。作品透过对春宝娘的“母性”心理刻划,展开了对摧残人性的非人道现象的批判。作品浓重渲染“人”被作为“非人”(而不单是作为阶级人)的可悲境遇,故而能引起社会的普遍性同情,作品也就产生了极大的艺术力量。即便革命色彩很浓的小说,也有从人性视角透视人物心理的描写,使人物变得更真实可信。魏金枝的《奶妈》写女革命者的精神品格,便有很浓厚的人情味渲染。这位“奶妈”在临刑以前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再见一面被她悉心抚育过的孩子,提出的理由很简单:“虽然我是个共产党,难道共产党就没有亲戚、朋友,以及一切人情的事么?”这是很精彩的一笔:唯其不违言人情、人性,这样的共产党人才是有血有肉的,才能真正打动人们,赢得人们的尊敬。像这样灌注鲜明人性、人道内涵的作品,在左翼作家创作中并不罕见,这应当是审视、评价左翼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以往人们谈人性、人道而色变,对左翼文学评判大抵缺失这一视角,这实在并非公正之论。
注释:
①姚辛:《左联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②杨义:《中国小说史》第2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参见《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上海《社会新闻》1933年3月3日。
④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⑤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全集》第20卷第4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⑥鲁迅:《集外集?题〈彷徨〉》,《鲁迅全集》第7卷第150页。
⑦鲁迅:《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为美国〈新群众〉作》,《鲁迅全集》第4卷第2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⑧[美]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第29页,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⑨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第136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⑩《浙江党部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1928年3月16日)》,《浙江革命档案选编》第34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1许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迹?在宁海中学》,《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
12参见郑择魁等:《左联五烈士评传》第85—86页,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
13徐梵澄:《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4茅盾:《〈地泉〉读后感》,《茅盾全集》第19卷第3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15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第238页。
16《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载1931年11月《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
17艾青:《诗论》第2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8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4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