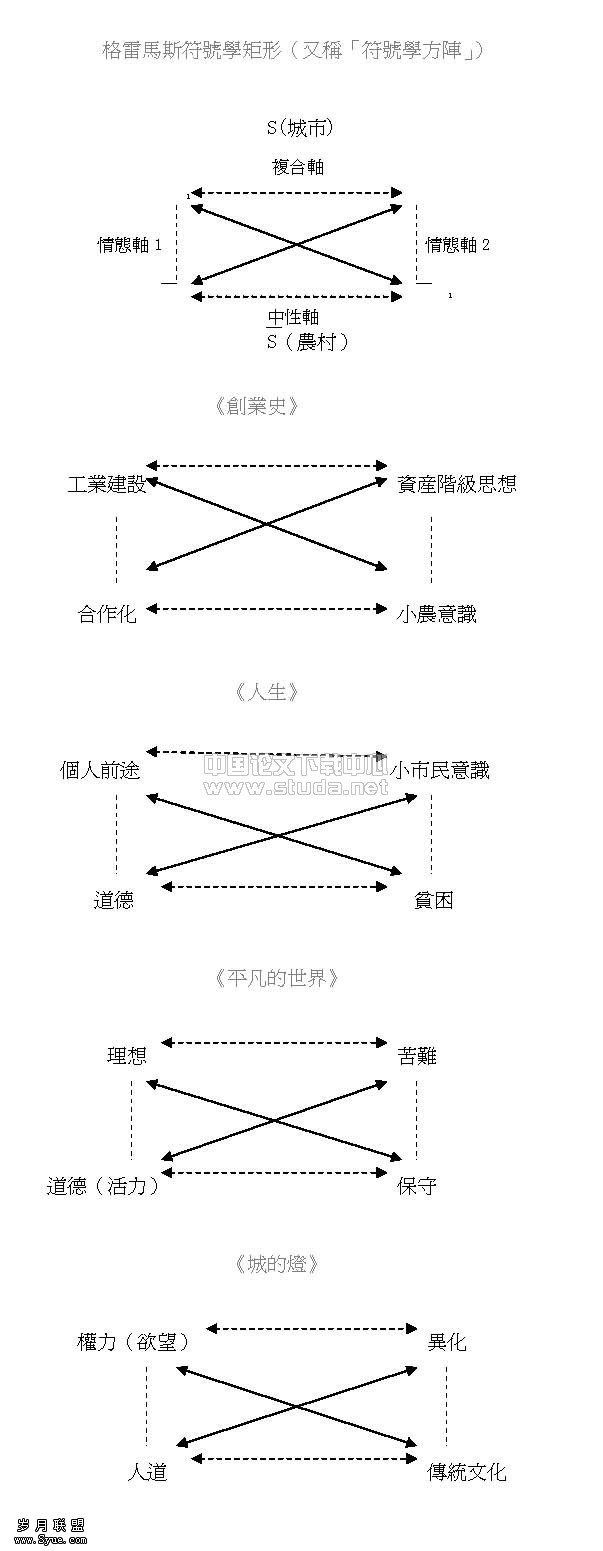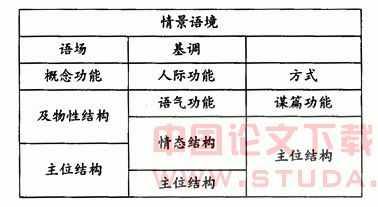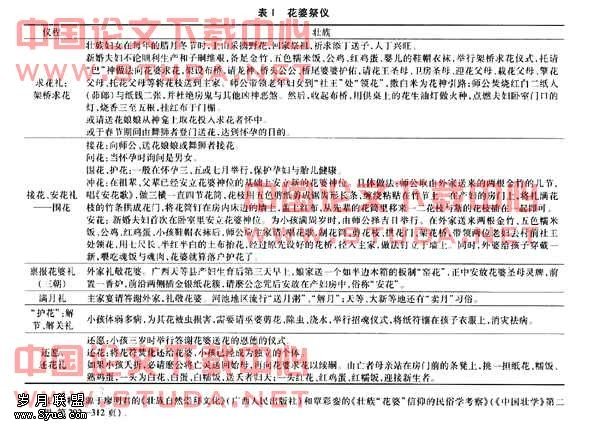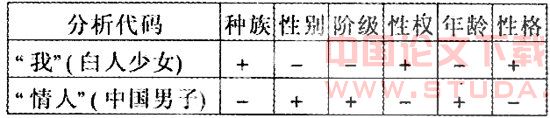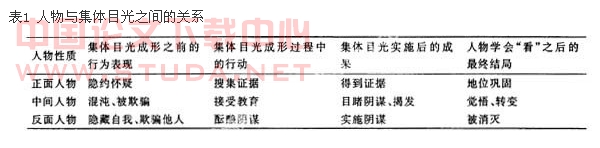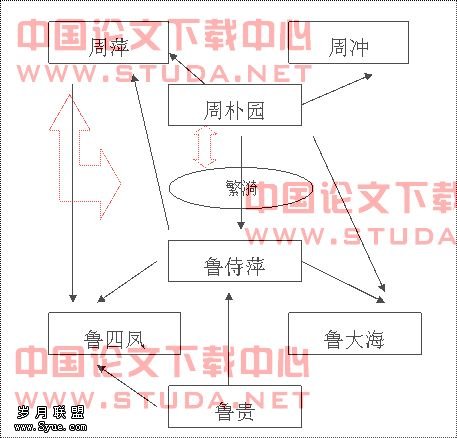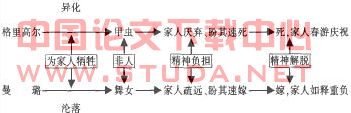体验与旁观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3
一、体验式的写作与客观式的考证
传记写作一般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作者带着极大的人生体验去感悟笔下对象的生活,在传记主人公的的身上融入了作者的人生体悟,“传记并不是纯粹的,它还需要表现传主的个性。”①带着这种情感体验写出来的传记往往更像散文或小说,容易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另外一种则是带着旁观者的姿态多方面搜集资料,将精力集中于不同说法的多方面的考证上,这种传记更利于学术研究。当然,这里的分类只是就倾向性相对而言,虽然,“传记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②事实上,任何好的传记作家都没法消除在传记中留下的自己的影子。可以这样说,肖凤的《萧红传》与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分别代表了以上两种倾向,这种归类并不是一种主观的猜测,从他们以下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们有着各自自觉的追求,肖凤在谈到她为什么写《萧红传》时说到:“写《萧红传》纯粹缘于某种情感的共鸣和共苦,因为我出生后到懂事起就没有见过生母……从那时起,我也就立志在文学的殿堂里诉说人生的经历、描写命运的曲折坎坷,讲述别人没有讲过的故事。”③因此,肖凤有感于自己与萧红命运的某种情感共鸣而试图“讲一个故事”。葛浩文在写《萧红传记》之前是系统学过传记文学课的,《萧红评传》的前身是《萧红略传》,而且这篇《萧红略传》是在柳无忌老师开的传记文学讨论课上的发言,④在《萧红评传·中文版序》中葛浩文还谈到:“但是我写不下去——那一刻,我已在不知不觉中抛开了过去我所接受的以客观、理智态度从事学术研究的训练,不知怎的,我竟然觉得如果我不写这最后一行,萧红就可以不死。”⑤可以看出,葛浩文是以一种“从事学术研究”的态度来对待《萧红评传》的,他有意识地排斥自己情感的介入。
从某种程度上说,传记属于文学,从而有了“传记文学”这一词。罗兰·巴特说过:“文学是语言的冒险”,甚至还有学者提出“语言就是文学本体”的观点,的确,语言本身对文学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肖凤的《萧红传》与葛浩文的《萧红评传》的语言风格完全不同。《萧红传》为了表达那种血泪交加的“身世之感”需要采用散文式或诗歌式的抒情语言,它的语言更像是一部散文或小说的语言,或慷慨激昂,或缠绵婉转。而与之相对,葛浩文《萧红评传》中的语言则较为“中性”,朴实无华,娓娓平缓,完全是一种学术的语言,也没有像《萧红传》中那么多带有情感色彩的形容词。
《萧红传》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头的:“美丽的松花江啊!北国的江!你的甘甜的乳汁,哺育了多少智慧、勤劳的儿女。你有源远流长、永不枯竭的生命,你可曾知道,你的一个聪慧、软弱的女儿,早殁于千里之外的异乡……”⑥与其说这是传记不如说是一首散文诗。同样是开头,同样写萧红出生的地方,葛浩文则采用了以下的方式:“东北大平原位于中国本部的北方。西连蒙古边缘的大兴安岭山脉,北接西伯利亚,黄海和朝鲜半岛是它东南方的屏障。”⑦这样的开头像是一个客观的地的介绍,丝毫没有介入自己的情感体验。因此,两篇传记从开头就有了截然不同的语言叙述特色。一开始的语言风格界定了通篇文章的风格。另外,肖凤的《萧红传》为了传达置身体验的情感,运用了大量的形容词,并且有些地方情景交融,栩栩如生,再现了一幅幅萧红生活的画面:“自由的大海的波涛,与自由的温暖的海风,在她的耳畔弹奏起了美妙的,她倾听着。在这种从未聆听过的美妙音乐的伴奏之下,她不由自主地默诵起了普希金的诗句来。”⑧这是描写萧红从东北到青岛的船上的情景,而葛浩文的《萧红评传》中写萧红的行踪经历带有“线索”的意味,没有点缀的形容词,也少有抒情性的文字,而只是用一两笔代过萧红的行踪,同样是写萧红从东北到青岛,葛浩文用以下几句话代替了肖凤的大段抒情:“二萧在大连停留了几天,大约六月初到达青岛,立刻搬进舒群为他们租好的房子。”⑨这几句话足以将萧红的行踪交代清楚了,葛浩文在感情渲染上并没有花费多大笔墨。
引文是反映传记作者资料来源的信息,我们透过引文能看出传记是以谁的观点为支撑(或是受谁的观点影响)的,拿前三章的引文做例子(前三章都是写到萧红去青岛之前的情况),粗略地统计,肖凤的《萧红传》共引用38处(除去有争议的看法中引用的资料),其中引用萧红或萧军的散文就达30处,而这30处又基本上引自萧红的散文,也就是说,关于萧红在去青岛之前的这段人生经历,肖凤是从萧红的散文中揣度出来的。而葛浩文写萧红这段经历时引文达42处(除去有争议的看法中引用的资料),其中引用萧红、萧军的散文仅15处,而且,葛浩文引用的资料范围较广。肖凤在写萧红去青岛之前的经历时除引用二萧的散文外,她的资料还来源于萧军、铁峰、舒群、丁言昭、傅秀兰的回忆,而葛浩文写这段经历时还引用了拉铁摩尔、端木蕻良、肖凤、萧军、张秀珂、铁峰、陈隄、何宏、许广平、傅秀兰、丁言昭、孙陵、骆宾基、舒群、石怀池、李洁吾、黄淑英、张琳、司马桑敦等人的回忆或他们写的有关萧红传记的材料。而且,葛浩文为了考证萧红的生平资料,在1973年到1974年间,还两次穿梭飞行于美国、日本、香港和之间,访问萧红生前的友好,搜求有关萧红的史料。对一些有争议的说法,比如萧红生母的死期和萧红上小学的日期,肖凤的《萧红传》中列出了两种观点,并引用了萧军以及铁峰的回忆,最后依据萧红的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得出结论:萧红九岁时生母去世。对这一个问题,葛浩文引用了丁言昭、陈隄、铁峰、肖凤、骆宾基等人的观点,最后同意了肖凤及陈隄的观点,他的依据是萧红的散文以及萧红的同学的回忆。另外,对于与萧红在东顺旅馆同居的青年是谁的问题,肖凤认为是萧红父亲为她订婚的人,并在后面注释中说:铁峰在《从呼兰到哈尔滨——萧红家世及早期生活的创作》一文中曾说,与萧红同居的不是汪而是别人,依据现在所见到的有关资料判断,此说似根据不足。但是,葛浩文认为萧红是与一李氏青年同居,他引用了石怀池、张琳、陈隄、骆宾基等人的说法得出他的观点,而肖凤在这个问题上,只用萧军的观点证实自己的看法。
以上两种不同的态度导致了他们整体阐述上的不同,肖凤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体验着萧红的人生经历,能引起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读肖凤的《萧红传》就像是读一篇凄哀的散文一样,从中读到的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事实也是这样,《萧红传》前两章最初就是发表在《散文》月刊1986年创刊号及2月号上的。而且当时读者的反应是:“许多素不相识的读者,从天南海北寄来了一封又一封感人肺腑的信件。他们中间有教师,有大学生,有工人,有农民,有战士,有医务工作者,有干部。他们在一封又一封感人肺腑的书信中,都不约而同地关怀着《萧红传》的写作,殷切地鼓励我共同努力。有的年轻朋友还与我坦诚地谈心,诉说自己的身世及内心感受。”《萧红传》成为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喜爱的读物,并引发了一些人的身世之感,它其中融入了肖凤的想象力的虚构,这种虚构也是必要的,“因为虚构的生活在我们看起来更真实……传记家的想象力不断受到激发,用小说家的——谋篇布局、暗示手法、戏剧效果——来拓展私生活。”{10}可以说,《萧红传》达到了一部散文或小说的效果,但是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情感共鸣,读者承认它是“翔实地考证了萧红的一生”。{11} 二、倾向性的评判与以文本为重的评论
肖凤的《萧红传》写于80年代的,虽然那时思想已解放,但长期形成的以政治眼光评判事物的思维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肖凤的《萧红传》中出现的政治性的字眼。相对于肖凤,葛浩文的《萧红评传》中对人对事的评价多选用中性的词语,对萧红作品的评价则偏重于文本本身。
肖凤的《萧红传》中介绍萧红的家世时,称:“七八十年前,呼兰县里住着一家姓张的大地主。他们的远祖原是山东省的破产农民。”{12}她用“大地主”称呼萧红的父亲及家庭,而葛浩文在介绍萧红家世时用了“乡绅之家”一词,无疑,两者相比,“乡绅”是一个中性色彩的词,而“大地主”则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化的称呼。肖凤的《萧红传》在介绍萧红在哈尔滨上学的情况时说:“‘五四’新文学与外国进步文学的熏陶,使萧红对旧中国的黑暗产生了敏锐的反感。这时候,在全国范围内,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反帝反封建的情绪普遍高涨,要求民主与的空气越来越浓厚,这种气氛深深地感召了萧红。她自幼在交织着爱与歧视的不正常的环境中长大,内心里对民主与平等有着自发的追求,时代的潮流特别迎合了她内心深处的愿望。从这时候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就在她的心里生了根,发了芽。”{13}肖凤在介绍萧红经历时用的是顺时的时间顺序,由下段的“1928年6月4日”可以知道,肖凤认为萧红在1928年6月前已经具有了这种“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但葛浩文却认为萧红在1928年底才首次接触到由“五四”运动所触发的青年运动,而且他认为萧红当时参加示威游行时对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感到恐惧,她是因为激昂的情绪和强烈的好奇心而加入到游行行列的。不管萧红当时的思想事实上怎样,他们的叙述话语是不同的。另外,对于萧红的一些反日爱国举动也被肖凤刻意渲染了,她写到了1938年萧红主张并集体创作成的农民抗日戏剧《突击》,并且讲到了《突击》受爱国群众的欢迎,而对这一出在文学成就上不突出的戏剧,葛浩文没有谈,他反而对萧红于1938年1月中旬参加的由胡风主持的讨论会上的发言大加赞赏,他详细引用了萧红的发言并表示赞同:即萧红认为住在城市并非是与“群众”脱节、与“生活”脱节。而对这一观点,肖凤没有提及。
对萧红作品的评价,两篇传记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但是他们两位的着眼点还是不同的。葛浩文在谈到《马伯乐》这篇小说时,曾经说:“撇开政治观点不论……”事实上也是如此,葛浩文对萧红作品的评价并不是从政治思想出发的,肖凤却是更倾向于从政治思想方面分析作品。对于萧红《生死场》的评价,肖凤将它看作是一部抗日爱国小说:“《生死场》是一部描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小说。”{14}葛浩文却认为:《生死场》是以哈尔滨近郊为背景,描写“九·一八”事件前后当地农家生活的一部小说。并且肖凤认为萧红在《生死场》中传达的精神状态是振奋的:“萧红抱着极为振奋的希望,描写了故乡的人民,怎样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起了消灭侵略军的英勇斗争故事。”{15}肖凤认为这是萧红的本意。葛浩文认为虽然这部小说在当时的确产生了抗日的效果,但是他认为:“作者的原意只是想将她个人日常观察和生活体验中的素材——她家乡的农民生活以及他们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情况,以生动的笔调写出。”{16}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肖凤对于萧红作品的评价多侧重于政治思想方面,但有时有脱离文本之嫌,而葛浩文却是从文本出发体会作者的本意,没有做政治性的比附,可以说,他对萧红《生死场》的评价比较接近于我们今天的观点。另外,葛浩文对萧红作品中的文笔以及结构等都有中肯的评价,而肖凤关注的似乎只是在于作品的主题思想以及社会意义方面。
对于自己所写传记的意义,肖凤在《萧红传·序》中说希望:“自己挚爱着的祖国,在向四个化进军的进程中,涌现出更多有才华的女诗人、女小说家、女剧作家、女散文家和女文学评论家,为我们民族的文学史,增添出更加美丽的色彩。”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中文版序》中说:“如果这本书能进一步激起大家对她的生平、文学创作和她在现代中国文学史所扮演角色的兴趣,我的一切努力就都有了代价。”从这两段序言中可以看出,肖凤希望的是通过她的《萧红传》激励人民有萧红式的爱国热情,为祖国的建设努力,而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希望引起人们对萧红创作的关注。
三、“以善为本”的评价与“直陈是非”的评论
肖凤在传记中继承了中国“与人为善”的传统,同时她也没法摆脱现实微妙的人际关系,她对笔下人物持着隐恶扬善、宽容达观的态度,她尽量回避传记中人的弱点与不足,而或许因为葛浩文是美国人,可以以更超然、冷漠的姿态静观传记中人的善与恶、美与丑。
肖凤在《萧红传》中写到萧红、与萧红有关的人物以及评价萧红作品时,是本着“以善为本”的原则的,而葛浩文的评价却有“是非分明”的意味,他不仅写到了他们“善”的一面,对他们身上的瑕疵也进行了揭露甚至是批判。这也许真的归因于他们身处异国,有些东西在肖凤那里“不能说、不便说、不愿说”。
两篇传记都对萧军做了介绍,肖凤《萧红传》中的萧军“是一个倔强豪爽的青年,中等偏低的身材,肩膀非常宽阔,方方正正的白脸膛上,长着一双细眯的小眼,眼睛上面横着两条向上挑起的剑眉”。{17}在这里,萧军是一个豪爽、耿直、正义的形象。在葛浩文的《萧红评传》中,萧军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的:“萧军生得短小身材(身高近五尺三寸),国字脸,目光锐利加上咄咄逼人的弯弓眉,性格粗暴,酗酒、口角、打斗。”{18}这里的萧军身上增添了“霸道”的色彩,其实,根据黄淑英、孙陵等人的回忆,萧军的脾气确实暴躁,甚至于动手打萧红,肖凤的《萧红传》回避了萧军性格上的弱点,她只写出了萧军身上侠义、豪爽的一面。同时对萧军、萧红、端木蕻良之间的纠葛,肖凤并没有追究太多,从肖凤的《萧红传》中看不出其中的是是非非,但是葛浩文在他的《萧红评传》中透露了萧军对端木蕻良那种轻视、谩骂的态度。
端木蕻良在萧红的人生历程上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在肖凤的《萧红传》中出现的端木蕻良只是萧红身边的一位伴侣,而在葛浩文的《萧红评传》中端木蕻良有很多的弱点,葛浩文引用聂绀弩的回忆,说萧红常向聂绀弩抱怨端木蕻良是个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在靳以心中,端木蕻良是个自私、矫饰的懒虫,靳以还记得有一次端木蕻良在他的面前毁谤萧红的作品。对这样事情肖凤只愿取人身上善的一面,她回避了他们身上一些弱点,葛浩文则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他们的性格。
作家传记不可能回避作品不谈,虽然肖凤以《萧红传》为名,葛浩文以《萧红评传》为名,但其实,二者都对萧红的作品进行了评论。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肖凤对萧红作品的评价受当时中国评论界的影响而且只言其作品好的一面,对其中的不足之处很少提及。比如对《商市街》的评价,葛浩文一反当时中国评论界的观点,认为《商市街》值得重视,并从多个角度评价了这部作品。对《生死场》的评价,肖凤认为它显露了一位女作家的才华,小说里有诗一样的感情,肖凤对《生死场》的评价都是正面的评价,葛浩文肯定了这部小说的成就之后,他同时也指出《生死场》在结构与修辞上的不足,并认为如果从纯文学的观点来看,《生死场》要算部分失败。
四、结语
对上述比较,本文无意比较孰优孰劣。他们都对萧红研究起了推进作用。肖凤的《萧红传》是国内第一本较为详细的萧红传记文学,她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切身体会萧红的悲苦,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虽然这部传记存在着在今天看来并不成功之处,但是肖凤的写作离不开中国80年代的大环境,我们不能苛求作者。在西方汉学家中,葛浩文是耀眼的一位,他把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翻译介绍到西方,对西方汉学的起到了瞩目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他几十年来对萧红的兴趣有增无减,他致力于萧红作品的翻译与萧红生平的研究,“葛浩文博士的著作《萧红评传》,无论就其内容的启发性还是著作的影响力而言,它都是有史以来萧红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19}他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比较客观地考证了萧红的一生,对萧红的一些作品做出了超越当时中国评论界的评价,他的有些观点比较贴近于我们今天的观点。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①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9页。
②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胡适文存》,上海:亚冬图书馆,1930年,1088页。
③祖丁远《苦难也是一所大学——肖凤访谈录》,《百花洲》,2002年4月,106页~107页。
④⑤(美)葛浩文《萧红评传·中文版序》,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1页。
⑥⑧{12}{13}{14}{15}{17}肖凤《萧红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0年, 1页、49页、2页、17页、54页、55页、22页。
{10}Virginia Woolf,The New Biography,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Books, 1927, p.1~6。
{11}{19}李向辉《批评的批评:萧红研究回顾》,《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163页。
⑦⑨{16}{18}葛浩文《萧红评传》,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8页、40页、53页、27页。
上一篇:萧红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