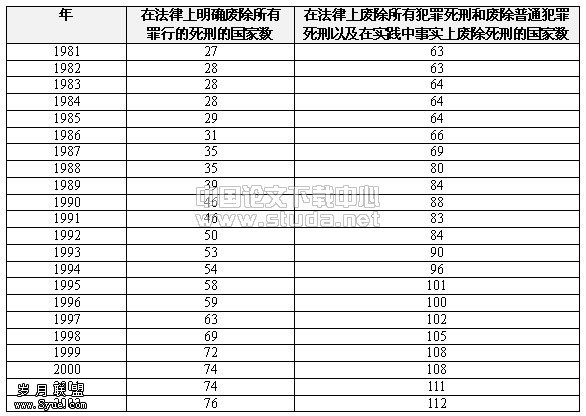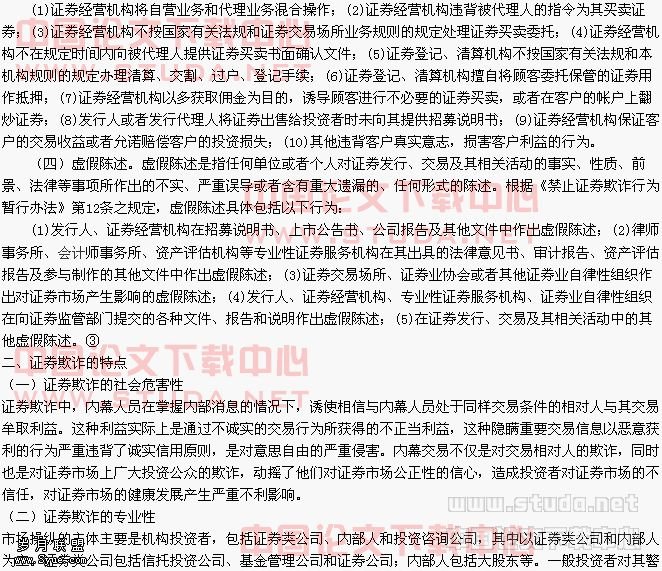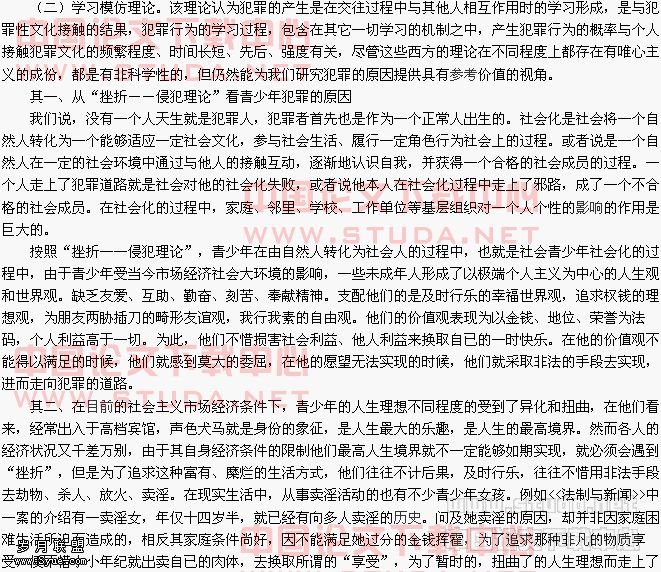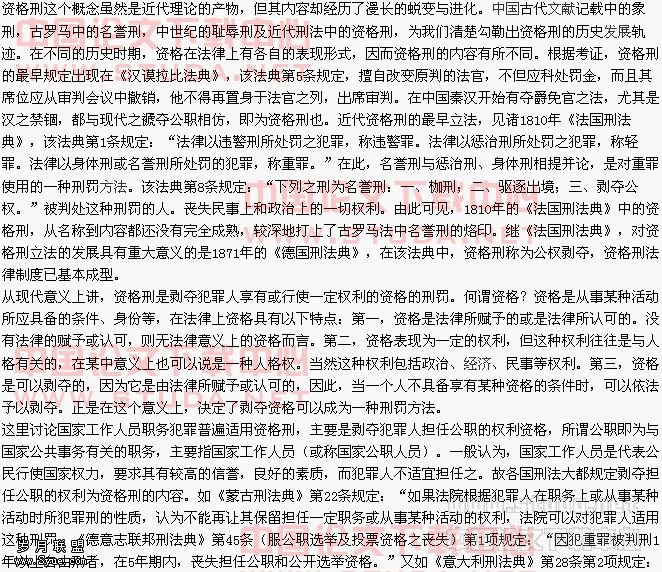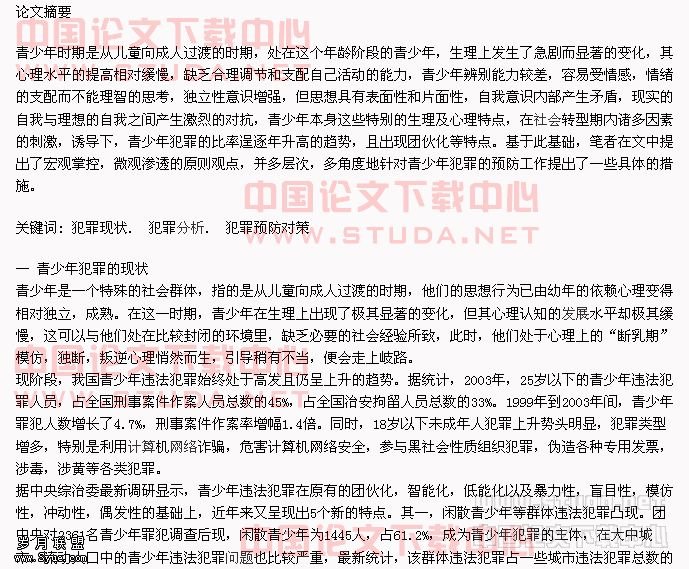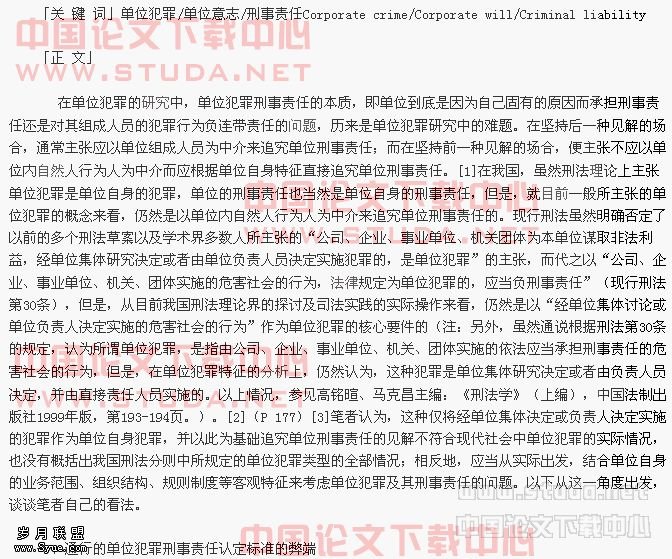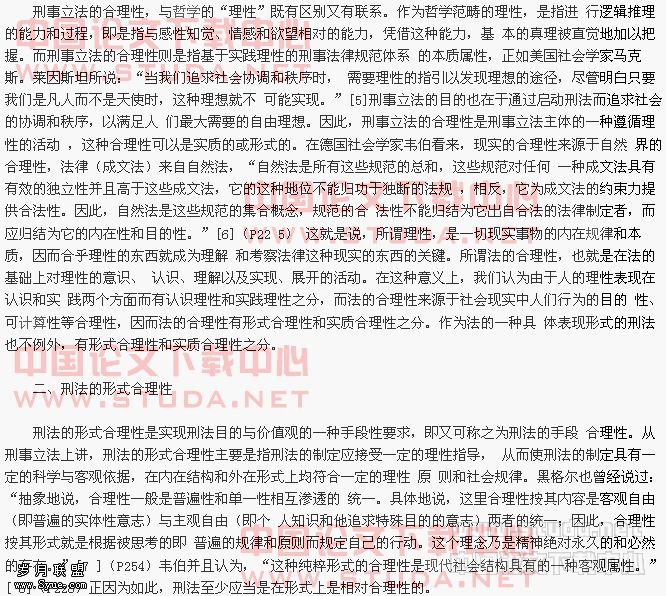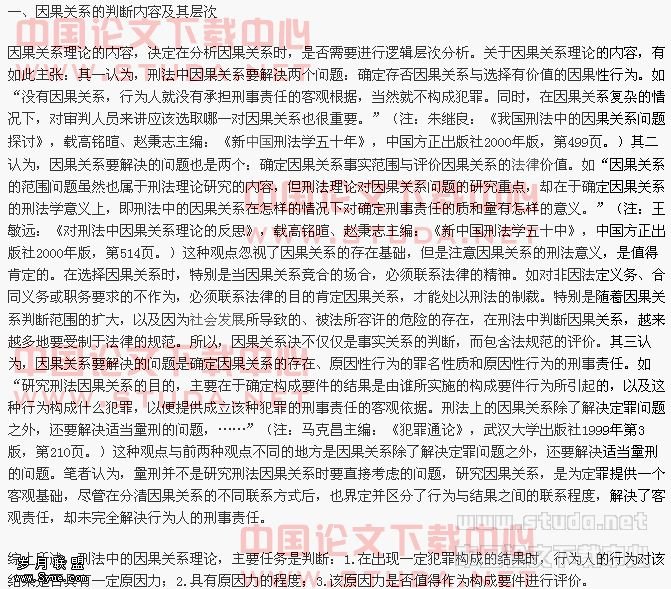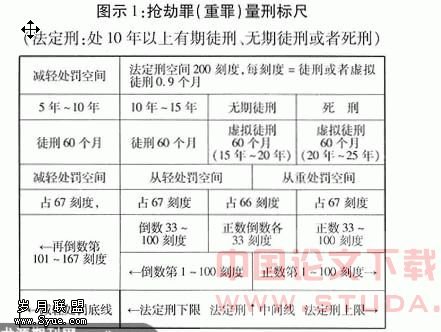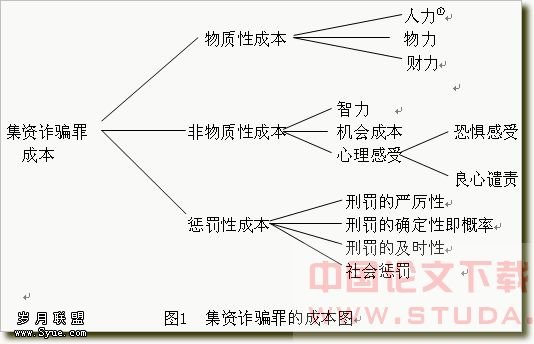“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司法适用中的困境与对策
摘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曾被誉为“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但由于条文本身的缺陷和配套制约机制的不完备,这把锐利武器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反而在司法适用中陷入难堪的困境。本文分析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司法适用中陷入困境的原因,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司法适用 困境 完善对策
一、尴尬与无奈的现实困境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早出现在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并为1997年新刑法所吸收。1997年刑法第395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显而易见,该条款是立法机关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日趋严重,特别是少数官员聚敛巨额财富却无法查明其真实来源状况而采取的立法措施,立法目的明确,针对性很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弥补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漏洞,严密法网,被寄予期望,有的学者将其誉为“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1]但综观近年来司法实践,这把“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并未能发挥理想的效用,反而在一定意义上不但成了一些不法分子逃避打击的“保护伞”,而且还“意外地”保护了行贿者,处于十分尴尬与无奈的难堪境地。
2001年1月23日,曾引起国内媒体关注的“批发乌纱帽”的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常委王虎林被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数罪并罚执行8年;其妻张玉梅被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2]王虎林夫妇有存款368.96万元,美金7662.14元。减去合法收入67万余元,及受贿的5万元(1992年8月,王虎林曾“帮助”私营山西泰和高科技生物工程研究所解决资金问题,研究所负责人张志文为“感谢”王虎林,送给王虎林5万元人民币。),还有296万余元和美金7662.14元,不能说明来源。法院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王虎林有期徒刑3年,其妻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300余万巨款是不义之财,联想到他大肆突击提干、疯狂卖官(王虎林1983年10月至1999年5月曾先后任壶关县委书记和长治县委书记,因在调升长治市市委常委之前的短短两个月内突击调整干部420人,提拔干部207人而被组织查处和舆论曝光。)就不难理解这钱的来由。法官以刑法第395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王虎林有期徒刑3年,是调不出半点毛病的。利用这一条款,不仅王虎林逃脱了以贪污、受贿罪判刑的更重惩罚,能全身而退,而且还保护了一批通过他买官的行贿者幸免于牢狱之灾,皆大欢喜。这个条款无形中助长了贪官们的嚣张气焰;因为贪得再多,只要没有证据,也只是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多判5年。[3]如此,“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却成为不法分子逃避打击的避风港。
出现这样尴尬与无奈的窘境,与刑法条文本身的缺陷和配套制约机制的不足有直接的联系,本文拟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司法适用中的缺陷作一些探讨,并提出修改完善建议,供立法者、司法者,并与研究者讨论。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司法适用中陷入困境的原因
依据刑法条文的规定,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经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的,方成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判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管数额如何巨大,只能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4]正是由于立法条文本身的缺陷以及适用保障机制的漏洞,导致被誉为“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适用中陷入困境,难以发挥威力。
(一)主体范围界定不当:刑法规定本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行为人正是因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可以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受贿,敛取不义之财,损害公务廉洁性和党与政府威信。司法机关如有证据证明与国家工作人员合法收入差额巨大财产是贪污、受贿所得,自当以贪污、受贿罪处罚;若司法机关不能查明来源,行为人也不供认的,当成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样定罪依现行刑法对现职国家工作人员来说是适当的,但对于离、退休公职人员突然暴富,又无合法财产来源的,却无可奈何。当前贿赂犯罪手段越来越狡猾、隐蔽,不易被发现。确有一些公务人员任职期间接受他人请托,为其谋取利益,退职后收受贿赂,对这种行为最高司法机关解释 (2000年6月30日通过,2000年7月2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 认为可构成受贿罪。但如没有受贿证据,虽然退休公职人员财产或支出明显超出其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也不能成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只能作无罪处理。另外对在职时贪污、受贿,但将所得转移他处,退休后取回该财产一夜暴富的,如无贪污、受贿证据,现行刑法也不能追究。立法上限定本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现职国家工作人员),无疑在暗示国家工作人员临退职之际接受请托,为他人谋利,退职后收受贿赂;或者乘在职时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毁灭罪证,转移财产,待退职后取回,只要没有证据,就可高枕无忧,颐养天年。而事实上,又会有哪个行贿者愿意主动投案检举贪官,又有哪个贪官会自首认罪呢?
(二)财产难于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依据在于其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数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司法机关也未能查清其来源。当今许多国家或地区规定了严格的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公务人员要廉洁奉公,恪尽职守,认真履行定期如实申报个人财产状况义务,如公务员不能对其收入不相称之财产作出令人满意之解释说明,就要受犯罪指控。而我国虽然早在1988年就设置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罪名,但直到1995年5月才出台《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0年4月1日起,个人储蓄存款帐户才要求必须持个人身份证办理,实施实名制,更是迟至2000年底才将财产申报制度扩大到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的家庭。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我们对于党政领导干部是否存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问题,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前置制度,只能依靠对他们的消费情况“望闻问切”去“透过现象看本质”,一旦遇上守着金山哭穷的“藏富不露”的贪官(现实当中,这类有着“清官”之誉,结果却被发现是个大贪官的现象并不少见。),我们就毫无办法了。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上述一系列廉政规章制度颁布之后,我们至今也仍然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和一套法定的程序,依据这些规章制度来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对各级党政官员及其家庭的真实收入情况进行调查。这也就难怪,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独立发挥作用,而贪官们也总是在其他严重罪行被揭露之后,才被发现他们原来聚敛了如此天文数字的财富。即使目前严格执行财产财产申报制度,也只能及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的家庭,而在这一范围之外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中,大贪官也大有人在,河南省荥阳市财政局原局长(科级)薛五辰从1994年11月到1998年4月,贪污受贿230余万元,另有600多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5]缺乏有效的监控官员财产和发现其非法巨额财产的机制,难以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真实财产状况,一个腐败分子如不是因为在其他犯罪行为上“做事不密”而东窗事发,纵使他聚敛了惊天的财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也适用不到他头上。
(三)刑罚畸轻:刑法规定本罪的法定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罚畸轻,易导致如下弊端。
1、刑罚畸轻,罚不当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聚敛钱财,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几百万之巨,这些不义之财可能是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所得,但因司法机关不能掌握其贪污、受贿证据,本人又不供认的,只能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论处,在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幅度内处刑,与其犯罪危害极不相称,罚不当罪,会轻纵犯罪分子。
3、容易滋生新的司法腐败。受到贪污、受贿罪指控的国家工作人员相当一部分身居要职,拥有复杂的关系,犯罪手段隐蔽,难以查获。如被告人拒不供认巨额财产来源,司法机关办案人员接受贿赂,放弃侦破案件的努力,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结案,轻纵犯罪分子。再有一种,就是检察官、法官手下留情。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查处大要案,涉及干部太多,不利于一个地方的稳定,因此在查处一些大要案时,能保护的干部尽量保护起来;而让贪官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就可以让一些行贿者隐蔽下来,不受法律追究。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一些司法人员从“维护”地方“稳定”出发,明智地选择了尽快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方式来结案,既让贪官免于贪污、受贿罪的重惩,又“保护”了行贿干部,维护了地方“稳定”。本来是为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严密法网而设立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了滋生新的腐败的漏洞。
另外,本罪仅对犯罪人非法所得予以追缴,并无财产刑处罚,也是轻纵犯罪分子的缺陷所在。
三、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司法适用的对策建议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要真正发挥其严密法网,打击贪污受贿犯罪的积极作用,应弥补立法缺陷,完善配套支持措施,保障这把“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能真正发挥威力。
(一)立法改进
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每个国家都存在,并且都有怀疑政府官员的巨额财产是贪污、受贿所得,但却无法查清贪污、受贿证据的现象,为遏制这种现象,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反腐败法案中规定对国家公务人员拥有无合法来源巨额财产的以犯罪处罚。如我国香港地区1971年《防止贿赂条例》,巴基斯坦1947年《防止腐败法》,印度1988年《防止腐败法》,泰国1975年《反贪污法》,新加坡1972年《防止贿赂法》等均有相关条文规定。讨论我国刑法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缺陷改进,笔者认为香港地区《防止贿赂条例》的规定值得借鉴。该《条例》第10条“拥有无法解释之财产罪”规定:(1)任何人士,如属政府雇员或曾为政府雇员,而——(a)所维持之生活标准,高于与其现在或过去薪俸相称之标准者;或(b)所支配之财富或财产,与其现在或过去之薪俸不相称者,除非能向法庭作出圆满之解释,说明其如何能维持该生活标准,或如何能支配该等财富或财产,否则即属违法。……该《条例》第12条规定:本罪项一经公诉定罪,可处罚款100万元及监禁10年,一经简易程序审讯定罪,可处罚款50万元及监禁3年。同时,还要将无法解释之财产或财富的金钱额缴付政府。从条文上可以看出,该条例规定“任何人士、如属政府雇员或曾为政府雇员”拥有无法解释之财产的,均可成立本罪,既可打击现职政府雇员贿赂犯罪,又可防止政府雇员在职时贪污受贿,并转移所得财产,退职后取回该财产;或者在职时接受请托,为他人谋取利益,退职后收受贿赂,逃避法律制载的行为,使政府雇员能恪守廉洁义务。“拥有无法解释之财产罪”的刑事责任,该《条例》规定,经公诉定罪者,可处罚款100万元及监禁10年,经简易程序审讯定罪者,可处罚款50万元及监禁3年,而对其他贿赂犯罪除《条例》第3条“索取或接受利益罪”,可处罚款10万元及监禁1年外,经公诉定罪者可处罚款50万元及监禁10年,经简易程序审讯定罪者,可处罚款10万元及监禁3年。比较一下,显然“拥有无法解释之财产罪”刑事责任重于其他贪污、受贿犯罪。那么,对于政府雇员或曾为政府雇员之人士,拥有与其薪俸不相称之财产,如能交待是贪污、受贿所得,则处刑相对较轻,如拒不交待来源,或编造虚假来源,则会招致更重处刑。在此《条例》中,“拥有无法解释之财产罪”严密法网,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作用得到发挥。
借鉴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立法经验,笔者认为我国刑法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作如下修正:(1) 完善主体规定,将退职国家工作人员纳入本罪主体范围,打击国家工作人员在任职时贪污受贿,转移财产,待退职后取回;或者在职时接受请托,为他人谋利,退职后收受贿赂,从而逃避法律追究的侥幸心理,以此来进一步遏制现职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犯罪行为,充分保障国家公务的廉洁性。在目前社会转刑时期,本罪主体范围可以较宽,规定为现职、退职国家工作人员。社会体制改革完成,公务员制度完善以后,笔者以为,贪污贿赂犯罪,包括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应限定为国家公务人员。(2)提高本罪法定刑,分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两款量刑,并加处罚金与没收财产刑。使腐败分子借拒不交代赃款来源,司法机关也无从查获其贪污受贿犯罪证据,从而换取法律轻惩的幻想破灭。让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真正成为“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
(二)完善配套措施建设
1、认真贯彻执行实名制,对违规金融机构坚决予以处罚,中央银行完善联行查询系统,保证个人存款帐户真实性。彻底打消腐败分子通过银行储蓄藏匿赃款的念头。
2、设立不动产真名制,增加不动产产权透明度。破灭腐败分子利用购置不动产转移赃款,毁灭证据,逃避法律追究的幻想。
3、建立完善的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作用,联合国社会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编的《反对腐化实际措施手册》指出,一是可以事先警告和预防,据此可以看出一个公职人员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是否与其收入相符,如不相符,即可要求其作出解释,或对其进行监督观察;二是在明知公职人员有腐败行为但查不到证据的情况下,仍可就其来源不明的财产对其提起诉讼。我国的廉政建设急需确立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据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1994年初已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项目,目前,有关部门正抓紧调研起草工作,也许不久就会出台。
笔者认为,如果立法缺陷得到改正,有强有力配套措施支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将会真正成为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开创一个廉政建设新局。
:
[1] 储槐植.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N].法制日报,1989-12-15(3).
[2] 武建中、李东升.山西长治原市委常委王虎林渎职受贿被判刑[N].法制日报,2001-1-29(1).
[3] 晓民.别给贪官留空子[J].民主与法制,2001,(9):33.
[4] 高铭暄、赵秉志.新编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998-999.
[5] 李东红、宋超.当局长不到三年 敛财却近千万[N].河南法制报,2000-1-27(1).
[6] 马倩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探析[A].杨敦先、周其华、姜伟.廉政建设与刑法功能[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