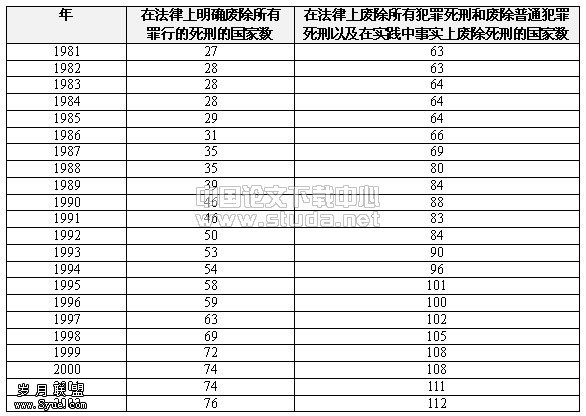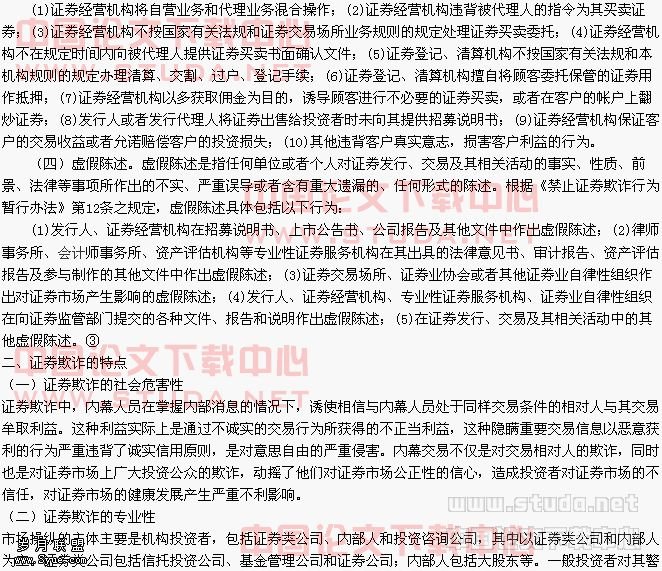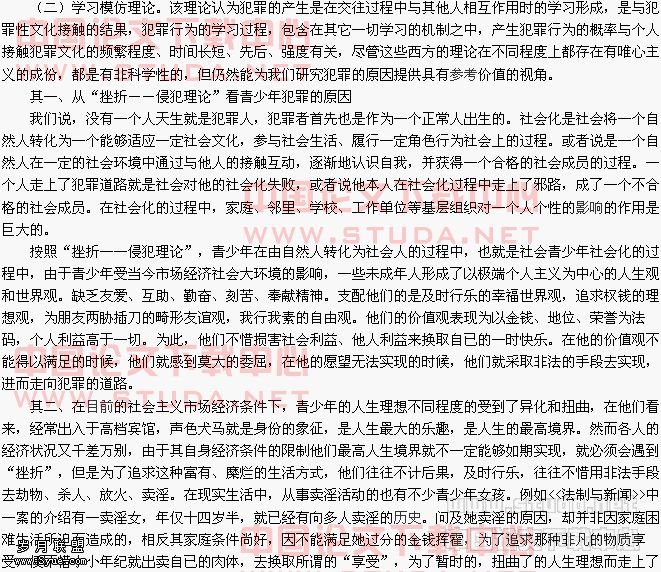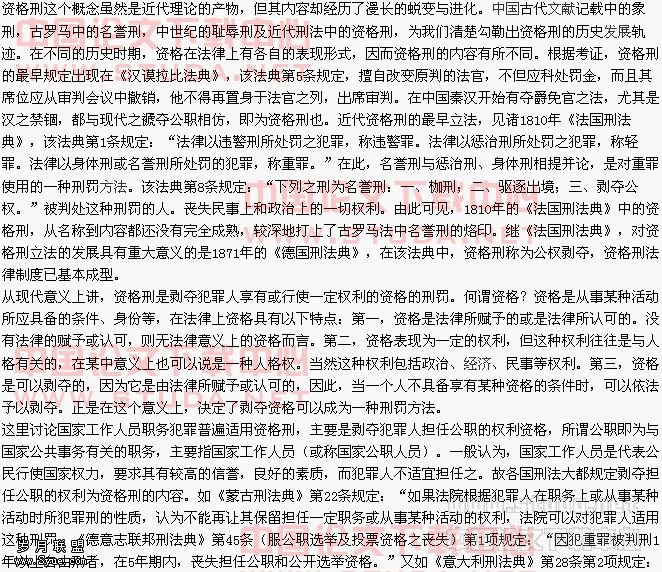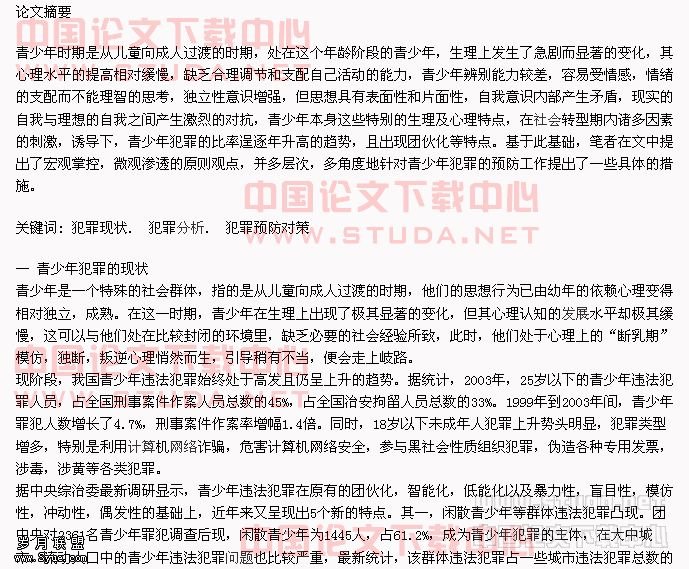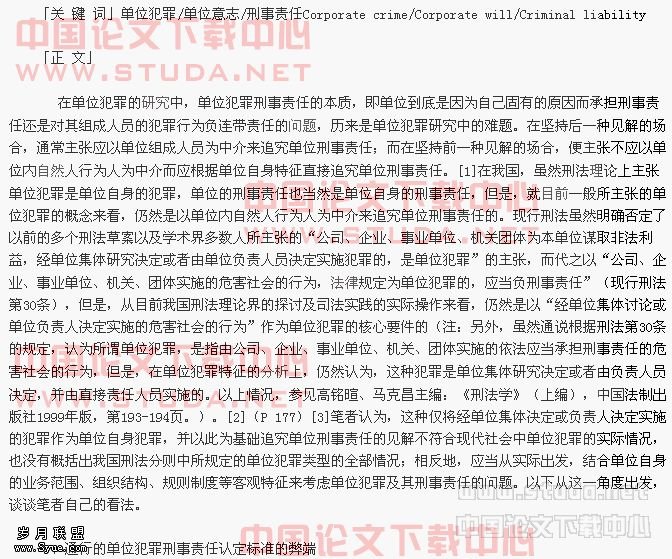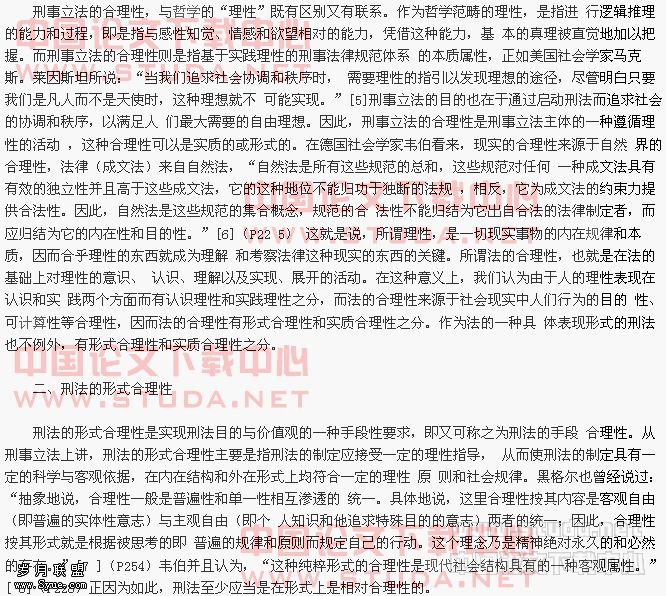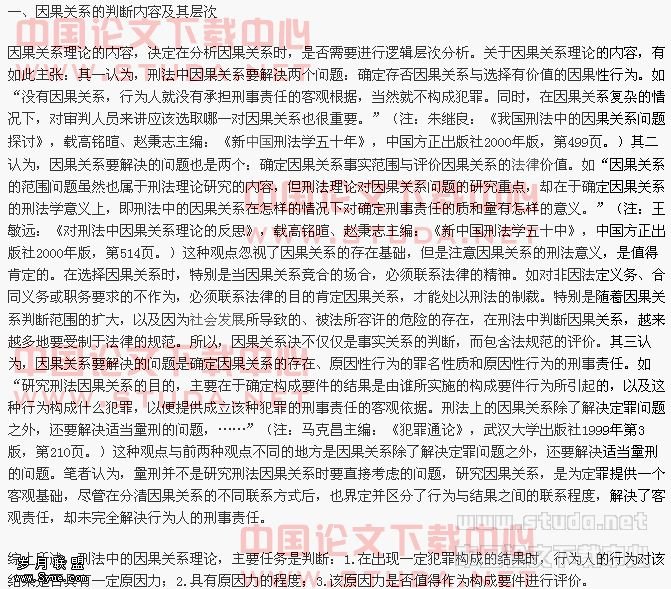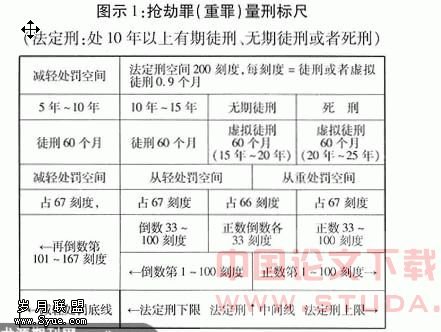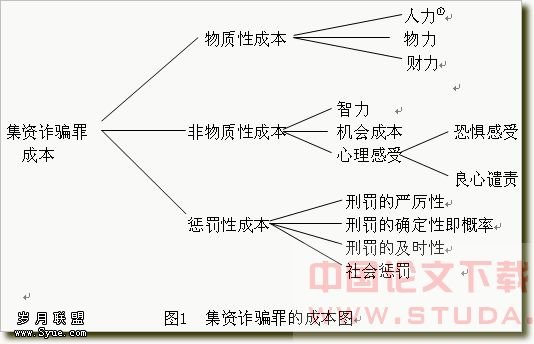窝藏、包庇罪行为对象——“犯罪的人”含义辨析
摘要:1997年刑法第310条窝藏、包庇罪的行为对象是“犯罪的人”。何为“犯罪的人”,我国刑法学界通说观点认为“犯罪的人”是指真正的犯罪人,即必须是触犯刑法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既包括犯罪之后潜逃在外,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的人或未缉拿归案的犯罪分子,也包括已被拘留、逮捕、判刑劳改,而后越狱逃跑的犯罪分子。本文认为通说观点值得商榷,若依据通说观点,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则认定窝藏包庇罪成立必须首先经有效判决确定被窝藏包庇对象有罪,这样做于司法实践不便,不利于保障司法活动顺利开展。通过借鉴国外相关问题立法状况与理论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需要,作者认为窝藏、包庇罪行为对象“犯罪的人”应包括真正的犯罪人和正在受侦查、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以经过有效判决确定有罪为必要,只要对他们进行窝藏、包庇的,即成立窝藏、包庇罪。
关键词:窝藏包庇罪 犯罪的人 含义 理解
一、存在的问题
我国1997年刑法第310条规定的是窝藏、包庇罪,该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支持、协助、配合司法机关依法对刑事案件开展侦查、起诉、审判活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而窝藏、包庇犯罪分子的行为,有助于犯罪分子逃避应得的制裁,直接阻挠和破坏了司法机关揭露和惩办犯罪分子的正常活动,从而给犯罪分子继续作恶造成了可乘之机。因此,惩罚窝藏、包庇罪犯的行为,对于保障司法机关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正常活动,公民积极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罪的行为对象,条文已示明,是“犯罪的人”。何为“犯罪的人”,我国刑法学界通说观点认为,“犯罪的人”必须是触犯刑法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既包括犯罪之后潜逃在外,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的人或未缉拿归案的犯罪分子,也包括已被拘留、逮捕、判刑劳改,而后越狱逃跑的犯罪分子。至于他们犯的是什么罪,可能判处或已经判处什么刑罚,则不影响本罪的成立。但在量刑时,可以作为重要情节给予考虑。如果窝藏、包庇的对象不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而是只有一般违法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人(如劳教人员和行政拘留人员),不构成本罪。[1]
依通说观点,窝藏、包庇罪行为对象——“犯罪的人”,必须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真正犯罪人,既包括犯罪后畏罪潜逃的犯罪分子,也包括被司法机关依法羁押后又脱逃的已决犯和未决犯。要认定窝藏、包庇罪成立,则必须首先确定行为人窝藏、包庇的是犯罪的人,如果不是犯罪的人,则不成立本罪。
在法律上认定某人是犯罪人,必须经人民法院有效判决确定。《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窝藏、包庇罪中的“犯罪的人”是否必须为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定的犯罪人呢?如果窝藏、包庇对象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无罪,窝藏、包庇行为是否还是犯罪呢?
薜某是某市财政局局长,因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逮捕,薜某之妻因涉嫌包庇薜某之罪行也被逮捕。案件开庭审理6天前,薛某突然在被羁押的看守所内死亡,“死因不明”。现对于薜某之妻是应撤销案件,还是应继续提起公诉,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意见不一,一方认为,薜某已死亡,不能再经依法判决确定为犯罪的人,薜某之妻包庇罪证据不足,应撤销案件;另一方认为薜某之妻确有包庇罪行,应提起公诉,案件陷入僵局。
这起案件争议关键即在于窝藏、包庇罪中行为对象“犯罪的人”应如何理解,我国目前尚无这方面的司法解释,国内书刊文章也未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司法实践所以在此问题上无法律依据或意见,造成适用上不便。笔者认为有必要借鉴参考国外立法与理论研究成果,就我国刑法上“犯罪的人”应如何理解作一探讨。
二、国外相关的立法状况与理论简介
在外国刑法学上,窝藏犯人一般称为隐匿犯人罪,是指隐匿犯人或者脱逃的人犯或使之隐避的行为。[2]如日本刑法第103条规定,藏匿已犯应当判处罚金以上刑罚之罪的人或者拘禁中的脱逃人,或者使其隐避的,处2年以下惩役或者20万元以下罚金。
本罪的行为对象是犯人或者脱逃的人犯。这里的犯人是指犯了罪的人,司法机关是否开始对之进行刑事追诉、是否已经判决等,均在所不问。犯人是犯了罪的人,那么如何理解这里的“犯了罪的人”呢?第一种理解是“犯了罪的人”是指真正犯了罪的人。因为如果所隐匿的人不是真正犯了罪的人,就谈不上侵害了国家的司法作用(没有违法性);再者隐匿不是真正犯了罪的人,在人情上是难免的,因可期待可能性很低(缺乏有责性)。
第二种理解是,“犯了罪的人”包括真正犯了罪的人,以及在隐匿行为的实施阶段,根据客观的、合理的判断,能够有把握地怀疑为真正犯了罪的人。
第三种理解是,“犯了罪的人”不限于真正犯了罪的人,还应当包括受到怀疑而处于侦查或追诉过程中的人。[3]
隐匿犯人罪只能由故意构成,行为人必须明知自己隐匿的是犯人,那么这里的犯人是隐匿犯人罪行为人判断认识的对象。上述三种理解,前两种理解对行为人来说,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隐匿的是“真正犯了罪的人”;而第三种理解是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隐匿的是真正犯了罪的人和正在受到司法机关怀疑被侦查或追诉的人。
日本刑法学上对于隐匿犯人罪的对象,就存在犯罪分子是仅限于真正犯人呢还是除此以外也包括因嫌疑而受到搜查、追诉的人的争论。前一种观点认为,从日本刑法第103条的文理上或者在实质上看,藏匿、隐避无犯罪实据的分子,无显著的违法性和责任性,隐匿犯人罪的对象即“犯了罪的人”应限定于真实犯了罪的人,但没有必要经过判决肯定本犯有罪。在对藏匿者的审判中,只有认定本犯确有犯罪的可能性才是正确的。反之,后一种观点认为本罪的主旨不在于犯人从刑罚上逃避责任,而是妨碍司法权的行使,把正在搜查、追诉中的分子藏匿起来,在妨碍司法作用这点上跟真正的犯人是一样的。后一种观点是多数的观点,日本刑事判例也采取这一立场。
所以,就少数论的立场来说,虽仅限于真正犯人,但多数论和判例的立场则认为,要包括真正犯人和因嫌疑而受搜查和追诉的这两种人。若是把正在搜寻和追诉中的分子藏匿起来的话,这种人犯即使后来成为无罪或不予起诉,也不会影响藏匿罪的成立。[4]
本罪的行为对象除了犯人之外,还包括脱逃的人犯,即在拘禁中的脱逃人。对“拘禁中的脱逃人”来说,是指根据法令被拘禁的人,不一定仅限于根据刑事手续而拘禁的人。[5]脱逃的人犯除了自己脱逃外,被抢夺的也包括在内,至于这些人以后是否被判有罪,或处以何种刑罚,则对成立本罪没有影响。[6]
受刑法学说和判例的影响,日本1974年改正刑法草案第159条藏匿犯人罪之条文中就规定,对于已犯应当判处罚金以上刑罚之罪的人或者罚金以上刑罚之罪的被告人、嫌疑人,予以藏匿或者使其隐避的,处3年以下惩役或者10万元以下罚金。申明了藏匿犯人罪中犯人的含义,既包括真正的犯罪人,也包括正在被搜查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另外意大利刑法(1968年10月修正)第378条(庇护他人)规定,对触犯法定刑为无期重惩役或轻惩役之人,协助其脱免官署之调查或追捕、而非该罪之共犯者,处4年以下徒刑。关于其他犯罪或违警罪者,处20万里耳以下罚金。被援助者系非可归责者或查明未犯罪时亦适用本条规定。也在立法上确定包庇犯罪行为的对象“犯罪的人”之含义,既包括真正的犯罪人,也包括正在被搜查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借鉴国外立法和理论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我国刑法上窝藏、包庇罪的对象“犯罪的人”应作扩张解释,其范围包括真正的犯罪人(犯罪后畏罪潜逃的犯罪分子、被司法机关依法羁押后又脱逃的已决犯和未决犯),正在受侦查、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以经过依法判决确定有罪为必要,只要对他们进行窝藏、包庇的,应成立窝藏、包庇罪。
这样理解“犯罪的人”的含义,笔者认为(1)符合立法目的,保障司法权威;窝藏、包庇罪属于妨害司法活动罪,行为人的窝藏、包庇行为妨碍和阻挠了国家司法机关对罪犯进行侦查、追诉、审判和执行刑罚的司法活动。刑法上设立窝藏、包庇罪正是要保证司法活动正常开展,重点不在于防止“犯罪的人”逃避责任。窝藏、包庇正在受侦查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窝藏、包庇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真正的犯罪人一样,危害司法活动,应予以惩处。
(2)符合客观认识,便于司法适用。窝藏、包庇罪是故意犯罪,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窝藏、包庇的是“犯罪的人”,如果将“犯罪的人”限于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真正犯罪人,行为人就不仅要认识到是受侦查、追诉的,而且要认识到是真正的犯人。尽管知道是受侦查、追诉的,但却误信其是无辜的时候,故意就要受到阻却,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如在偏僻丈夫杀死与人通奸的妻子,族长暴力干涉族中寡妇改嫁,当他们受侦查、追诉时,窝藏、包庇行为人会认为其行为正当,予以包庇、窝藏,阻碍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如将“犯罪的人”理解为真正的犯罪人和正在受侦查、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此问题迎刃而解。
(3)与刑法条文规定相吻合。我国刑法学界通说观点均承认脱逃的人犯是窝藏、包庇罪的行为对象,[7]刑法第316条规定,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脱逃的,构成脱逃罪,他们是当然的脱逃的人犯。罪犯是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定的真正的犯罪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不等于真正的犯罪人,成立脱逃罪不要求是真正的犯罪人,[8]即脱逃的人犯并不限于真正的犯罪人。承认窝藏、包庇脱逃的人犯成立窝藏、包庇罪,也即在实质上表明窝藏、包庇罪行为对象不限于真正的犯罪人。
刑法第362条规定,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等单位的人员,在公安机关查处卖淫、嫖娼活动时,为违法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310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实际上把涉及卖淫嫖娼活动的违法人员纳入了“犯罪的人”范围,这是国家出于打击卖淫嫖娼违法犯罪活动需要,在立法上设定的一个特例。
如果窝藏、包庇对象的犯罪经过时效,或该对象所犯之罪属亲告罪,被害人撤回告诉的,因没有对窝藏对象所犯之罪追诉处罚可能性,在这些情况下,由于已经不存在侵害国家司法作用的可能,藏匿、包庇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
对于逃离依法进行的非刑事程序的被监押人(如治安拘留、收容审查、劳动教养)予以窝藏、包庇的,通说观点认为不成立窝藏、包庇罪,[9]这也是受现行立法规定所限。这种行为同样妨碍司法权的正当行使,甚至造成比较严重后果,如公安机关对某些犯罪可疑人员予以收容审查,侦破犯罪案件,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将逃跑的收容审查人员予以窝藏、包庇的,就妨碍了公安机关的案件侦查活动,并造成社会隐患。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在将来立法修改时应予以明确,可以参照日本刑法上藏匿、隐蔽“拘禁中的脱逃人”的方式加以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错案是难以绝对避免的,有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错误追捕,但只要明知是被司法机关侦查、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其窝藏、包庇同样妨害了国家司法权的行使,如情节严重,即使本犯被宣告无罪,仍可以追究窝藏、包庇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情节轻微,应当不作犯罪处理。当然国家应当通过不断完善法制建设、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在最大限度内避免错案的发生。
对于文中前述案件,虽薛某未经依法判决确定有罪,但其实施了犯罪行为,是“犯罪的人”,薛某之妻包庇罪仍应成立。
窝藏、包庇罪中“犯罪的人”如何认定,无明确依据,在适用上时常引起争议,笔者建议最高司法机关机关作出明确解释,以利司法适用。
: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法制出版社,1999.985.
[2] [3]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762,763.
[4] [5](日)木村龟二.刑法学词典[Z]. 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512,509.
[6] 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821.
[7] 苏惠漁.刑法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730-731.
[8] 张明楷.刑法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837.
[9] 王作富.中国刑法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