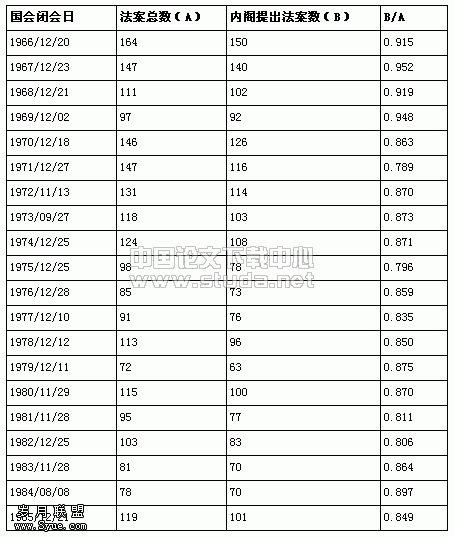司法场域中的非职业法官—— 一个初步的比较法社会学分析
【摘要】非职业法官是当前法律移植和比较法研究的一个热点。以美国和德国为样本的比较法社会学研究表明,非职业法官的类型选择与司法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运作中面临的问题以及现实需求密切相关,司法权力结构则深刻地影响了非职业法官在审判中的表现。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完善也应当具有一种全面的视角,既要认真对待当前的现实需求,也应充分考虑改革的空间、司法权力结构的影响以及相关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司法场域;非职业法官;陪审法官;参审法官;司法权力结构
【正文】
民众参与审判并享有一定的裁判权力,这在历史上由来已久并普遍存在于当今世界。然而,不同国家的政策、制度设计和实践千差万别,由此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非职业法官制度。随着现代法治的确立,这些未经系统法律学习和实践的民众能否适应日趋“形式理性化”的审判,已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是随着非职业法官制度被视为司法民主的“催化剂”而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引入甚至倚重,相关法律移植的效果如何,更成为比较法学关注的焦点。显然,这类问题的解答不能仅仅依靠抽象的理论分析,而必须借助法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以探寻制度形成的机理、运作效果及其制约因素。如果能在梳理各国制度设计和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对司法场域中的非职业法官展开比较分析,或许能够发现影响非职业法官类型选择以及非职业法官在审判中的表现的某些经验性因素。这些经验性结论不仅能在整体上增进我们对非职业法官的认识,同时也能为考察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状及其改革方向提供更全面的视角。本文即是沿着这个方向的初步努力。
一、分析框架与研究进路
(一)分析框架:司法权的地位与司法权力结构
鉴于深层次的司法理念、法律传统、宪政结构、社会环境等宏观因素,以及非职业法官的选任、诉讼程序、法官和律师的态度和行动等微观因素,都可能影响非职业法官的类型选择以及非职业法官在审判中的表现,在展开比较法社会学分析之前,有必要从这些因素中确立适当的分析框架。
从理论上看,审判独立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素,司法场域中的行动者应当只受法律和程序的约束。然而,只要不沉迷于“用逻辑的事物代替事物的逻辑”,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独立在任何国家都并非绝对,都无法摆脱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外界因素的限制。一方面,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司法受制于其服务的目标,容易受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格局的影响;[1](P3-11)另一方面,由于自由裁量权以及判决对后续案件的影响,审判可能突破个案限制从而对社会秩序格局造成重大影响,这使得“所有政权,不管其政治色彩如何,都希望司法机构在保有其独立的同时,不偏离公共秩序业已认可的概念太远。”[2] (P113)这些外界因素不仅型塑了司法权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以下简称为司法权的地位),同时也深刻地决定了包括非职业法官在内的司法程序参与者的命运。例如,夏皮罗(Martin Shapiro)发现,西方国家往往通过创设司法官员的选拔、培训、组织和升职体制等方式以确保法官在涉及政权利益的案件中的绝对忠诚。[3] (P46-50)达玛什卡(Mirjan R. Damaska)的法律程序类型学也表明协作式权力组织结构对非职业官员和权力平行分配的偏好,以及科层制权力组织结构对裁判者职业化和严格等级秩序的追求。[4] (P12-22)
当然,对于任何运作正常的司法来说,外界因素直接作用于司法程序参与者都是无法接受的,这已经触及司法正当性的底线。在法治理念被广为接受的今天,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重新型塑的过程”也就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外界因素并不采取直接、武断的方式来干预司法,而是通过法律职业者的资格要求、审判权的限定和分配等司法权力结构来实现间接控制。此外,尽管“程序正义”或“程序自治”的实现需要具备某些社会和制度条件,但程序一旦确立和运作,确实可能获得某种自主空间,并非完全亦步亦趋地跟随政治格局、意识形态等外界因素的逻辑进行。[5] (P1-36)所以,司法场域中的非职业法官固然无法超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他们直接面对的却是影响其处境及权力行使的各种司法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不仅包括司法权力配置等正式权力结构,正如下文将看到的,还包括职业法官与非职业法官的关系等非正式权力结构。
事实上,司法的运作主要涉及“如何运作”和“在什么范围内运作”内、外两个面向(图1)。就外部而言,司法权的地位是司法权与其他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反映了历史传统、社会经济、意识形态、政治格局等外界因素如何决定司法的运作范围、自主程度和司法参与者的类型,以及如何通过“重新型塑”赋予司法过程以基本权力结构。作为外界因素在场域内的整合,司法权力结构规定了司法程序参与者可能的行为及其限度,同时也可能赋予行动者以某种背离外界因素的自主性,从而决定围绕事实认定、法律发现乃至纠纷解决所展开的对抗、合作和判定等场域内运作如何进行,甚至反过来影响司法权的地位。[6] (P813-853)通过对司法权的地位和司法权力结构的考察,我们或许能在整体上把握司法运作过程,从而对司法场域中的非职业法官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
(二)研究进路:现实的复杂性与类型化处理
由于各国司法权的地位和司法权力结构各具特色,在解决“比较什么”的问题之后,“如何比较”也就成为本文需要解决的另一个前提性工作。
从民众参与审判的程度和方式来看,非职业法官包括分工和混合两种类型,即陪审法官和参审法官。由于两者分别源自两大法系并基本延续至今,法系比较已成为非职业法官研究的一个惯常进路。[7] (P441 -581)不过,且不说法系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已略显不足,传统的比较法方法以及法系等范畴基本聚焦于私法领域,司法往往与国家权力结构密切相关而难以发现共同的传统,[8] (P39-40)法系比较无法化约各国非职业法官现象的复杂性。例如,俄罗斯、西班牙等大陆法系国家就引入了陪审团制度。[9] (P223-259)而在某些同属一个法系、非职业法官类型相同的国家,民众参与审判的方式和权限也有相当的差别,其实际效果更是大相径庭。
各国的非职业法官类型及其实践纷繁复杂,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全面的比较法社会学分析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如果不致力于建构这样的宏观理论,转而选择一些代表性国家进行比较,或许可以获得某些经验性结论。这种方法虽失之全面,却可以做出更为细致的分析,随着样本的累积亦能逐渐接近全面的认识。当然,比较样本的选择需相当慎重,不仅制度设计应具有代表性,还要能突显出不同的司法环境。此外,从获取有效信息的角度来看,非职业法官在实践中的适用亦不能过少。以此标准来衡量,美国陪审团制度和德国参审制度比较适合充当分析样本。
第一,从制度代表性来看,“一枝独秀”的美国陪审团作为陪审法官的分析样本应该不会招致多少疑问。但是,有学者认为,从是否合乎“民主、自由等共同基本价值”来看,法国参审制更具典型性。[10] (P206)应当说,民众参与审判确实承载着诸多价值追求,但以此作为代表性判断标准则有失偏颇。事实上,非职业法官既能成为自由和民主的捍卫者,也可能成为统治者的正当化工具,历史上并不乏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11] (P83-102)仅就制度设计而言,无论是非职业法官的资格和选任,还是法庭组成、非职业法官的职权及其行使,美、德两国的做法往往处于对立的两极,法国则位于两者之间。(注:例如,英美陪审团一案一选、随机遴选并保留无因回避。德国参审员则实行提名推荐,回避理由和程序与职业法官相同。法国参审员虽未奉行一案一选,遴选过程却更富民主性,而且控方和辩方分别拥有4次和5次机会行使无因回避权。再如,陪审团制度中非职业法官和职业法官的人数比例通常为12: 1;德国小刑庭和大刑庭中的比例分别是2: 1和2: 3;法国重罪案件初审的比例是9:3,上诉审中则是12: 3。)相对而言,德国参审制更适合作为本文的分析样本。
第二,从司法环境来看,除了民众参与审判的制度设计差异以外,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美、德两国司法权的地位呈现“回应型”和“自治型”两种向度,其程序运作也代表了当今世界的两种主要风格,例如民事诉讼“对抗式辩论原则”与“当事者主导原则”,以及刑事诉讼“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分野。虽然两国近年来在许多方面有所趋同,但在司法权的地位、司法权力结构及其背后的社会环境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具有比较法上的典型意义。
第三,从适用的普遍性来看,美国州法院和联邦法院每年的陪审案件分别超过150000件和10000件,“陪审团仍然决定时下最重要的问题。”[12] (P304)德国参审员除了广泛参与劳动纠纷、商事纠纷、社会福利纠纷、财税纠纷等专门案件的审判以外,参审的刑事案件占到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13](P179)从近些年的实证研究来看,参审法官发挥了其特有的作用。
二、司法权的地位与非职业法官
必须承认的是,司法权的地位涉及因素较为庞杂,难以找到面面俱到的比较框架。然而,不管是否奉行“三权分立”,任何国家都存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基本国家权力,三者的关系框架往往是历史传统、文化理念、利益集团甚至政党派别等外界因素相互博弈的结果(图1)。对于比较不同国家中司法权的地位来说,考察司法权与其它两种权力的关系不失为一个较好的起点。[8] (P11)
就此而言,从各国丰富的实践中不难识别出两种对立情形。一种情形下,司法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的界限分明,审判恪守法律与政治的区分,适用法律规范解决个案纠纷既构成对司法运作的限制,同时也赋予其抗拒外部干扰的保障。另一种情形下,司法权与其他权力并非那么径渭分明,审判能够超越法律规范和个案事实的束缚,回应社会需求乃至形成公共政策。鉴于比较法学者对此已有深入研究并提炼出“自治型”和“回应型”等经典术语,下文将援用这一框架。(注:参见[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78、 81-128页。类似的研究包括达马斯卡有关“能动型司法”与“回应型司法”的区分,等等。参见[美]达马斯卡:《司法与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145页。)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框架是对现实进行高度抽象的类型化操作,本文仅仅着眼于美、德两国司法权的地位的基本面貌,无法也无意做到事无巨细。
(一)自治型司法中的非职业法官:以德国为例
受启蒙思想以及法国大革命后宪制改革的影响,德国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宪政格局。[14] (P15-18)就立法与司法的关系而言,尽管德国的理性主义不像法国那样狂热,在启蒙主义影响渐起时受到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洗礼,意识到制定一个完整、连贯和清晰的法典并非易事,但他们仍然坚定地为这一目标而努力。[15] (P185-189)“法典至上”的观念以及德国法律人对“法律科学”的信奉,一方面要求法官严格遵守法律,甚至认为“任何司法解释皆为政治行为”;[16] (P186)另一方面也赋予了法官超越外界干预的自治性。这是因为在德国人的意识形态中,“政治乃至民主机制应当发生在法律颁行之前;法律颁行之后,法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17] (P248)
在德国,司法与行政的关系也深深地受到这种职业自治的影响,审判独立得到普遍尊重,“通常没有人去谈论法官的独立性问题,它是不言而喻的,属于社会意识”。[18] (P17)不过,对职业自治的珍视却促使司法与行政发展出千丝万缕的关系。法官普选制在德国人看来有违职业标准,会带来无法忍受的对政治的依赖。只有通过系统的法律学习、严格的司法考试和法官最初选任的幸运儿才能被任命为“见习法官”。可是,无论是法律教育的监管、司法考试的组织,还是法官选任的职业素养判断,州司法部都起着主导性作用。[19] (P143-148)经过3-5年试用期,绝大多数的“见习法官”会被任命为“终身法官”,从理论上看完全可以独立行使司法权力,但正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傅德法官所言,“只有少数法官愿意终身担任一个职务,大多数都会去争取获得一个更高的职位”。[18] (P9)这些为数不多的晋升机会却再一次被控制在司法部等行政部门手中。[19] (P145)布兰肯伯格(Erhard Blankenburg)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依照职业标准选任法官增强了司法相对于政治的自主性。可是,对职业标准的恪守也削弱了法律职业者获得民主正当性(democratic legitimation)的机会:德国的法官不是(像美国许多州的法官那样)尽力去获取民众的支持,而是不得不尽力迎合那些在其职业生涯中无处不在的行政控制。[17] (P269)
由此可见,德国的司法具有高度的自治性。理性主义、法典至上、法官选任和晋升的职业标准等确保了审判免受外界因素的直接干预和飘忽不定的民意的影响。审判必须恪守法律与政治的界限。与此同时,职业标准的行政控制限制了司法的运作空间,对社会秩序格局和法律的挑战必须通过政治渠道进行。或许,这正是“自治型司法”必须承受的“以实体的服从换取程序自治”的代价。司法权的这种地位对非职业法官的类型选择及其实践效果表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一,法律与政治的严格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德国采用参审法官模式。职业化的司法运作可能增大法院与社会的隔阂,需要民众参与审判以输入新的价值观,增强与社会的沟通而获取民主正当性。不过,非职业法官未在科层体系之内,国家权力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规训。如果他们拥有较为独立的审判权力,对裁判结果能发挥决定性作用,审判难免越过法律与政治的界限,这对于恪守职业自治、止步政治决定的德国司法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由此,一种既能彰显民主、转移压力,又不至于使审判失控的非职业法官类型最能满足其需要。这或许是德国历史上改陪审为参审的部分原因。(注:应当说,德国废除陪审制的成因是多方面,例如,作为替代物的本土参审制的迅速传播、“事实与规范”难以区分的固有认识、陪审被视为“法国输出的制度”而与其民族感情相悖,等等。然而,从当时大量有关陪审团制度内含对法官的不信任、放纵罪犯等批评中不难看出,法律与政治的区分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参见Francois Gorphe, Reforms of the Jury-System in Europe: France and Other Continental Countries,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27 (1936),pp. 157-159.)
第二,职业自治对德国参审员的来源及其代表性产生了深刻影响。德国法律要求参审员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参审员的代表性受到很大限制:其一,非职业法官未受系统的法律学习和实践,其能力容易受到人们的质疑,也不容易获得职业法官的信任。克劳斯(E. Klause)1972年对各地区法院中的124名法官的访谈表明,参审员的知识欠缺被视为参审制的最大弊端,40%左右的法官主张废除该制度。[13] (P180)其二,理解和适用法律对于参审员实非易事。在伦格尼(Christoph Rennig)1993年的访谈中,超过60%的法官和检察官抱怨参审员压根没有起到什么作用。[20] (P482)无论是基于对职业素养的推崇还是对民众参审难度的考虑,德国当局都竭力选择与职业法官有着相似社会背景和教育水平的人充任参审员。有关参审员社会结构的实证研究表明,来自社会较低阶层的人所占比例较小;年龄在40到50之间的人、男性以及公务员占的比例较大,尤其是公务员在选任过程中能够获得很大支持。[21](P453)在此,可以以德国联邦统计局1997年的数据为例说明(图2)。
第三,职业自治与外界干预的博弈影响参审员的表现。审判涉及纷争裁决和利益分配。利害关系人难免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审判结果,德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职业自治与外界干预的紧张关系。[17] (P248)虽然前文提到法官选任和晋升过程中的行政控制,但职业标准的强调使得外界力量的作用空间毕竟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参审制度就给了他们以可乘之机。德国参审员的预选程序基本控制在当地主要的政党、公职人员、工会、教会以及地方团体的手中。[22] (P194)不过,由于法官在法律知识、技能和经验上占据优势,他们往往利用民众的参与来抵抗外来干涉和行政控制。即如布兰肯伯格所言,“尽管众多参审员活跃在德国法庭上,但与其说法院和法官把他们视为对司法过程进行民主化控制的力量,还不如说只是把他们当作为司法运作提供抵抗外来干预的壁垒。”[17](P313)
(二)回应型司法中的非职业法官:以美国为例
美国也秉承了启蒙思想家的权力分立学说,其理解却不像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绝对。早在合众国成立前,美国人就已经意识到权力制衡的重要性。基于“司法机关为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的认识,[23] (P391)不仅司法独立以及法官的职位、薪俸等受到制宪者的高度关注并得到相应的制度保障,殖民时期的司法审查萌芽也经由马歇尔等人得以发展和巩固。法院能够对立法、行政等政府其他分支的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此外,虽然美国法官必须遵守立法,但这并未排除必要时对法律进行解释,这种解释有时已经偏离甚至对立法形成了修正。[24] (P22)从实践来看,美国的法院不仅可以在个案中通过违宪审查、法律解释等方式对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或政治问题施加影响,初审法院也可以通过在大量类似案件中做出相同判决以形成累积性司法决策。(注:参见G. Alan Tarr, Judicial Process and Judicial Policymaking, 2nd edition,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p. 284-299.该书对美国法院介入公共政策的途径进行了归纳,具体包括违宪审查、宪法补救(remedy)、制定法解释、行政行为审查、普通法裁判和累积性司法决策。)那些在立法、行政等领域失利的美国人往往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法院身上,通过发动相关诉讼来挽回颓势。(注:例如“行为修正模式”(Behavior Modification Model)、“公法模式”(Public Law Litigation Model)诉讼。参见Kenneth E. Scott, Two Models of the Civil Process, Stanford Law Review 27(1975),pp. 938-940; Abram Chayes, The Role of the Judge in Public Law Litigation,Harvard Law Review89 (1976), pp. 1288-1304.更一般的论述,参见[日]田中英夫、竹内昭夫:《私人在法实现中的作用》,李薇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应当说,司法权在美国社会占据如此显著地位,与其深受经验主义和普通法传统的影响密不可分。经验主义并不盲目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普通法传统并不通过立法或者其他方式明示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而是尊重民间社会规范,只有当人们既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平衡被打破时才给予法律的救济。从这个角度来说,普通法本身就是司法在回应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形成的。[25] (P111-241)由于遵循先例原则和严格的程序安排使得普通法国家在法律发展和政策判断上能够维持某种“一贯性”,灵活的区别技术则赋予法官较大的空间突破既有规则做出最适合特定情势的判决,这种渐进的生长方式(case by case)使得审判能够从容地面对外界压力,逐步形成公共政策并解决社会问题。
由此可见,美国的司法运作并非那么严格恪守法律与政治的界限,法院能够回应社会需求甚至介入公共政策,具有浓厚的回应性特征。虽然非职业法官与这种“回应型司法”的关系错综复杂,人们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上争论不已,(注:对立的观点,参见[比]卡内冈:《英国普通法的诞生》,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但历史或许就是一张“无缝之网”,[26] (P1)制度与制度之间、制度与制度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屡见不鲜。在不否认民众参与审判对回应型司法的塑造的前提下,后者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非职业法官类型及其在审判中的表现。
第一,司法正当性难题及其解决方式决定了美国对民众参与审判的强烈需求。基于司法在法律发展以及回应社会需求方面的重要作用,美国的法院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一个公共论坛,主要通过纠纷解决实现法律发展和国家治理。由此不得不面临一个正当性难题:如何维持“两造对抗、居中裁判”的三方结构而不致于使败诉方认为法院是其对手的同盟?依据美国学者的分析,该问题的解决主要包括同意模式和司法独立模式两种方案:前者是指当事人对解纷规范和解纷主体达成一致,败诉方基于自愿而不会把审判视为恣意武断;后者则注重司法的独立运作,避免法院社会结构从“三方”转向“二对一”。[3] (P2-12)非职业法官对两种方案的实现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一方面,民众参与审判有助于法院抵抗来自政府或者民意的压力,从而促进司法独立;另一方面,民众参与审判不仅增添了当事人选择解纷主体的机会,同时也能为审判输入为当事人所共享的社会共识、价值和道德观念,实际上也就是在解纷规范中添加了“同意”因素。由此,同侪审判观念在美国的深入人心、非职业法官的平民化和随机抽取、以及无因回避和陪审团搁置法律(jury nullification)备受责难仍顽强存在也就不难被理解。
第二,司法的回应性决定了美国采用陪审法官模式。民众参与审判能否起到补强正当性等作用有赖于具体的制度设计。鉴于非职业法官在法律知识和经验等方面远逊于职业法官,如果他们没有较为独立的权力,难免沦为陪衬,无法化解司法正当性难题。故此,民众参与审判必须握有职业法官不能完全操控的权力,采用分工式的陪审。与此同时,司法权的崇高地位以及判例法的“一次一案”为陪审法官握有如此大的司法权力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条件和制度环境。即便陪审团偶尔犯错或者偏离政治格局太远,个案的影响力一般都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并可以在后续同类案件中得到纠正。
第三,法律与社会的沟通深刻地影响了陪审员的表现。由于审判并不严格恪守法律与政治的界限,往往身处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博弈的中心,外界力量总是力图对司法运作施加影响。这不仅表现为法官选任浓厚的政治色彩,[27] (P44-46)还体现在不同种族、宗教、性别以及党派团体千方百计地对陪审员的资格、选任以及审判程序设计施加影响。这种博弈对陪审员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法官选任的政治性(尤其是在实行法官选举制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过度的“职业化”,法官并非那么绝对地按照法律职业标准的眼光看待陪审员,需要直面民众的反应,对被奉为“人民代表”的陪审员不得不表示一定的尊重。与此同时,法官可以利用陪审团实现自己的意图并影响社会,当争议问题过于敏感或者没有达成广泛共识时,法官在尝试做出回应的过程中也能借助陪审团缓解其面临的批评和压力。
三、司法权力结构与非职业法官
就司法权力结构而言,最明显的莫过于非职业法官的司法权力及其行使的制度安排,鉴于其体现在诉讼制度和程序规定中,可被称为正式权力结构。除此以外,职业法官的惯习等因素虽然没有形诸于制度,不容易为人们所察觉,却可能在职业法官和非职业法官之间形成一种“隐蔽”的非正式权力结构。由于任何话语机制都要依附于非话语机制才能得以运作和发生效果,[28] (P40-59)这种非正式权力结构对非职业法官可能会形成更细致或许也更深刻的影响。
(一)正式权力结构中的非职业法官
非职业法官在审判中的表现不仅取决于其享有的司法权力,也有赖于能否获得行使权力所需的案件信息,下文便从这两个方面揭示正式权力结构的影响。
1.司法权力配置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司法权的地位差异使得美、德两国分别采用分工和混合的非职业法官类型,其中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司法权力配置的差异。
首先,司法权力配置决定了审判中的权力制衡格局。从民众参与审判的程度来看,参审员对法官的制约似乎比陪审员更全面,因为前者与法官享有同等权力,后者只负责案件事实的认定。然而,如果考虑到知识和经验上的不对等,结论可能就不一样了。沃尔夫(Nancy Travis Wolfe)在德国统一前的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职业化程度较高的西德还是程度较低的东德,参审员都难以有效地参与审判。[29] (P511)而在陪审团审判中,“陪审团决定事实问题,法官决定法律问题”为审判中的权力制衡奠定了基本框架。尽管在实践中,法官可以通过运用证据规则、指示陪审团、指定裁决形式等方式制约陪审团的事实认定,但归根结底,陪审团才是事实问题的最终决定者。更何况,审判需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目光往返流转”,陪审团甚至可以在规范向个案下延的过程中,考量法官指示的法律,通过定罪、量刑和赔偿额度裁定等影响法官对法律问题的决定。[30] (P62-77)
其次,司法权力配置影响非职业法官能否在审判中独立行使判断。前述权力制衡状况多少已经说明这一点,但其影响还不限于此,评议规则和过程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混合式法庭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参审员人数居多,但由于其知识和经验上的不足,评议由法官总结庭审中的证据开始,参审员不得不依附于法官。即便有时候评议发生争议,法官往往能够利用其经年的法庭经验对参审员们分而治之,孤立异议者。(注:Stefan MACHURA, Interaction between Lay Assessors and Professional Judges in German Court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enal Law 72 (2001),p. 463.有学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此进行了模拟研究,结果发现,在由4名法律外行和1名职业法官组成的混合法庭中,评议前法官几乎都是少数派,评议后法官在每个案件中均胜出。参见R. Arce, F. Farina, C. Vila&S. Real,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Es-cabinato Jury System, Psychology, Crime&Law 2(1996),pp. 175-183.)反观陪审团,基于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大体分工,陪审团评议独立于法官,法官难以利用专业或者经验的优势影响陪审员的独立判断。不过,由于陪审团审判基本上实行“一致评议”原则,法官不参与评议过程也就无法有效地引导或者调和陪审员们的争议,以至于出现“陪审团僵局”(hung jury),极大地浪费了司法资源,增大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最后,司法权力配置在某种程度上还决定了判决说理和事后审查的方式。非职业法官没有受过专门的法律教育和实践,不太可能撰写充满法言法语的判决理由。鉴于陪审团与法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的基本分工,陪审团裁决无需说明理由,一般也不受事后审查。在参审制度下,撰写判决理由的任务只能留给职业法官,这就给他们留下了很大的活动空间。实证研究表明,德国的一些法官利用参审员的知识欠缺,背离评议结果而在撰写判决理由中掺入自己的主张。即便法官不背离评议结果,他们也能在宣布判决以及撰写判决理由时巧妙地将其不满告知当事人及其律师,以便接受上诉审查。[20](P481-494),[21](P464)考虑到“在德国几乎没有一个法官判决不被上诉”,[18] (P9)这对参审员的影响不言而喻。
2.案件信息的获取与验证
就案件信息的获取而言,美国的法庭主要依赖当事人双方的举证,通过高度制度化的辩论过程获取纠纷事实的信息。[31] (P29)陪审员无需事先了解案情便能够获得行使权力所必需的充足信息。德国的情形则恰好相反。大陆法系传统认为诉讼“即使开始纯粹是私人间的事务,一旦交给法院处理就变成了公共事务”。[32] (P25 -26)“审前证据的收集主要是(职业)法官或其它官员的职责”。[33] (P107)法官常会在庭审前详细研读材料并大致形成心证之后才开庭。由于担心非职业法官审前接触案卷材料受到“污染”,无法在庭审中保持公平公正,德国法官通常对此持否定态度。由此,法官和参审员在案件信息拥有方面极不平等:(注:在实证访谈中,参审员几乎同声抱怨无法获得足够的案件信息。参见Nancy Travis Wolfe, Lay Judges in German Criminal Courts: the Modification of an Institutio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38 (1994),p. 509.法官有时甚至利用这一点,精心地进行“审判准备”以便将参审员引向他们意图的结果。参见Stefan Machura, Interaction between Lay Assessors and Professional Judges in German Court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enal Law72 (2001),p. 457.)法官通过证据调查和审前研读案件材料,已掌握足够的信息甚至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基本看法;参审员往往只是在开庭前十五分钟或者半小时才来到法庭,基本上无法获取行使权力所必要的信息,更不用说挑战法官审前已形成的案件事实版本。(注:职业法官不事先接触材料也会出现类似状况。有学者曾邀请一些事先没有接触案件材料也不负责案件审理的法官来观察庭审,结果发现,“在26. 9%的案件中,旁观的法官和主审法官对司法判决有不同意见,前者更容易为辩方证词和其他证据的相互矛盾所困扰。” Thomas Bliesener, Lay Judges in the German Criminal Courts : Social -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the German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Martin F. Kaplan&Ana M. Martin eds.,Understanding World Jury Systems through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sychology Press, 2006, p.181.)
就案件信息的验证而言,美国主要依靠当事人双方的举证和质证,力图使裁判者接受己方构建的案件事实版本。基于司法的回应性以及纠纷解决的特征,即便案件真伪不明,裁判者也无须承担积极发现案件真实的负担,只需根据“盖然性占优势”或者“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做出裁决即可。陪审员既无需专门的知识就能在当事人对抗中验证案件相关信息,也无需额外探知案情就可以做出裁决。在德国,职业自治下的法官倾向于在做出裁决时已然排除怀疑、达到内心的确信,不太可能只是被动地在当事人及其律师的对抗中倾听和选择,也不可能接受美国那样较低的证明标准,在信息的判断以及事实认定方面承担了更大的责任。[34] (P201)他们常常只有在详细研究案件后才安排庭审,主持审判时会将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探究并印证存有疑问的事项上。[21] (P454)参审员事先对案件一无所知,只好在庭审中认真听取证言以了解案情。受庭审时间的压力以及法官主导程序的影响,他们几乎不可能形成和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所以,尽管德国法律规定参审员有提问的权力,但在现实中他们除保持沉默之外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