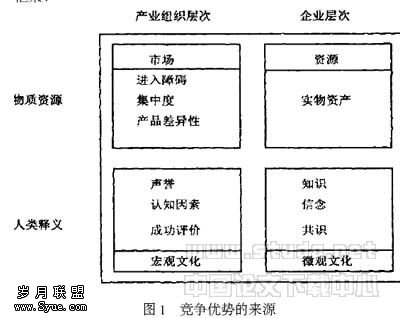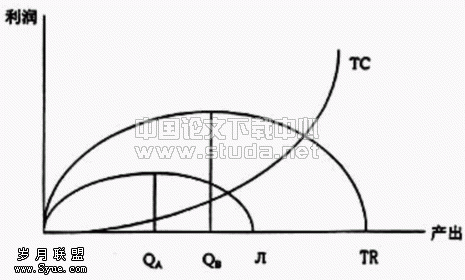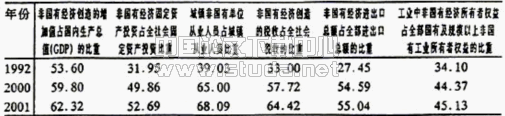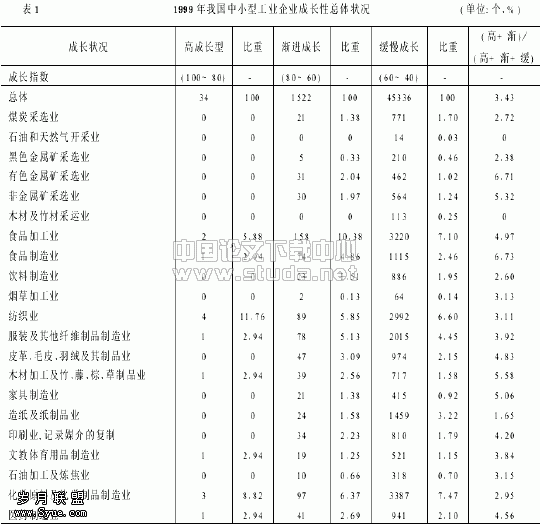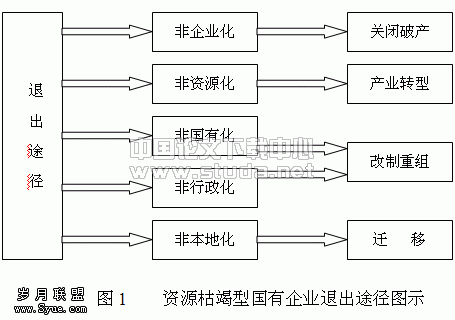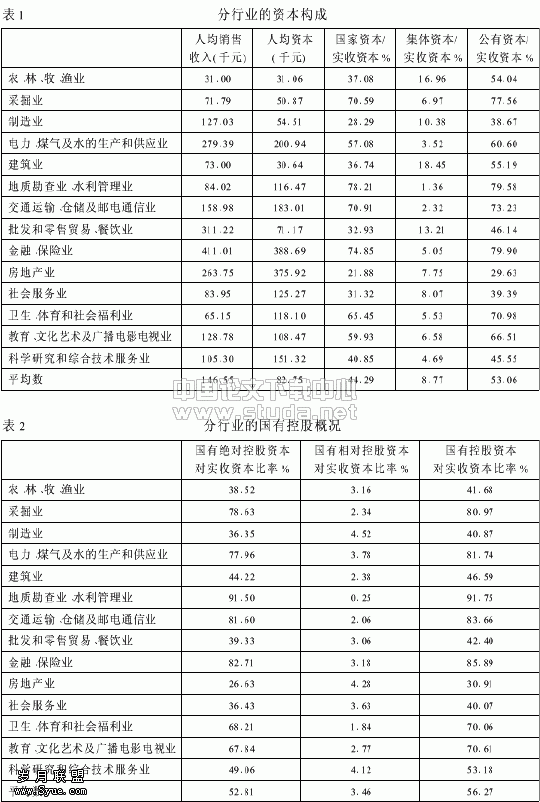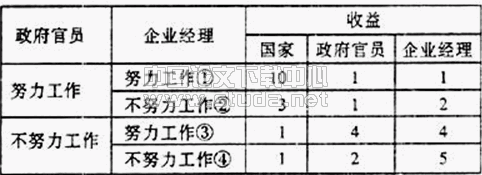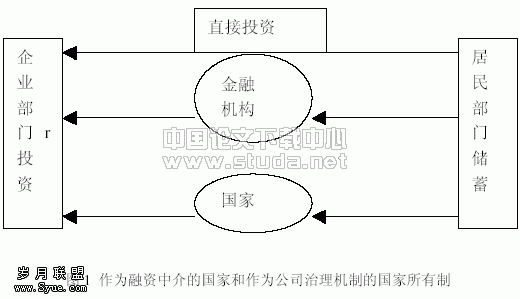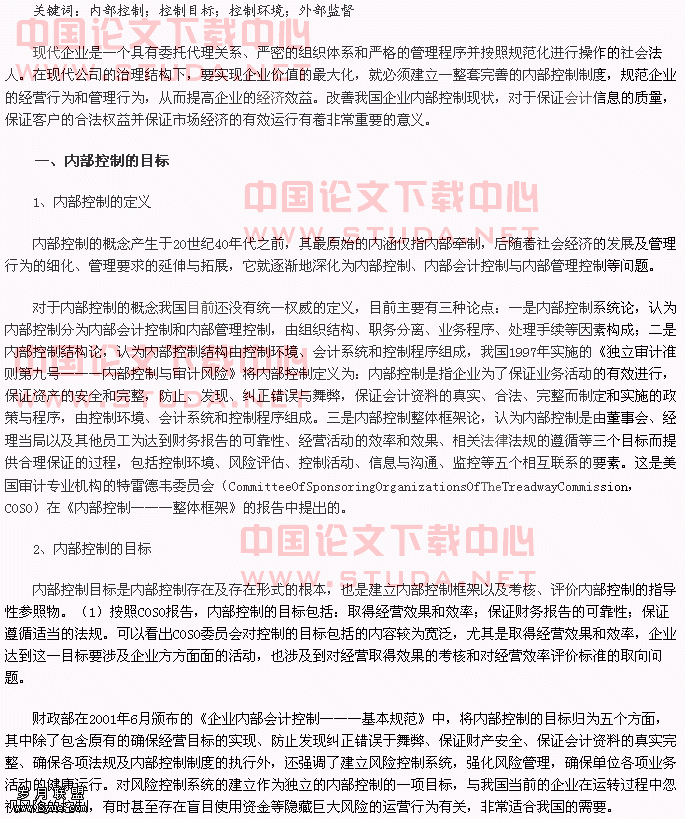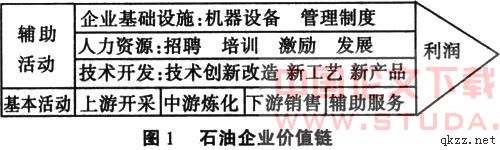路径依赖学说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內容提要:經濟變遷包括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路徑依賴最初産生於技術變遷分析,但在制度變遷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目前路徑依賴理論與進化論、博弈論等相互交融,在所有制和公司治理制度的多樣性分析中起著重要作用。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和公司治理改革是路徑依賴的,受到認知能力、經濟體制和因素等的影響,一旦外部環境發生變化,企業制度安排就可能趨同。
關鍵字:變遷;路徑依賴;進化博弈;所有制;公司治理
一、路徑依賴學說的起源和發展
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思想最早見於經濟史學家、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Paul A. David於1975年出版的《技術選擇、創新和經濟增長》一書,不過當時並未引起重視。八十年代,David與美國聖達菲研究所的W.Brian Arthur教授將路徑依賴思想系統化,很快使之成爲現代經濟學中發展最快、應用價值最高的學說之一。David的路徑依賴思想來自於他對打字機史的研究。
1936年,美國發明家Dvorak博士歷經十餘年的研究,發明了一種新的鍵盤,起名爲ASK鍵盤(美式簡化鍵盤,American Simplified Keyboard,後被稱爲DSK鍵盤),聲稱比打字機發明者、美國人Sholes 1870年設計的、現在通用的QWERTY鍵盤效率更高。據說,當初 Sholes 在研製打字機時,爲了解決打字員打字速度過快造成擠塞的問題,故意打亂了字母排列順序,而按照直到今天仍通行的QWERTY順序排列。不過,ASK鍵盤並沒有站住腳,慢慢地銷聲匿迹了,QWERTY獨霸鍵盤市場。David(1985)認爲,QWERTY鍵盤之所以能在市場上占統治地位,不是因爲它最好,而是因爲它最早。這種情況被稱爲路徑依賴。Arthur(1989)教授幾乎與David同時形成了路徑依賴的思想 ,但他的研究重點放在經濟中的遞增報酬與路徑依賴的關係。
David和Arthur的路徑依賴學說問世後,在經濟學家中産生了強烈的反響,許多經濟學家表示贊同,但也有些經濟學家反對。
1990年,美國德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的Leibowitz和Margolis批評了David關於路徑依賴的觀點,認爲DSK鍵盤比QWERTY鍵盤效率更高的斷言是由一些有欠缺和值得懷疑的證據支援的,而且,工效學的研究證明,Dvorak的發明並沒有太大的、科學上可以信賴的優點。QWERTY鍵盤只所以存續下來,不過是打字機生産者之間激烈競爭的結果,而不是所謂的路徑依賴。
從90年代開始,North、Stark、David 等人逐漸把路徑依賴研究由技術變遷轉向制度變遷,提出了制度上的路徑依賴理論。Campell、Hausner、Federowicz 、Vincensini 等人從生物進化的角度對制度性路徑依賴不同機制的解釋做出了貢獻。青木昌彥等人則試圖用進化博弈論解釋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
North(1990)認爲,制度變遷受四種形式的報酬遞增制約:(1)制度重新創立時的建設成本(set-up cost);(2)與現存的制度框架和網路外部性以及制度矩陣有關的學習效應(learning effect);(3)通過合約與其他組織和政治團體在互補活動中的協調效應(coordination effect);(4)以制度爲基礎增加的簽約由於持久而減少了不確定性的適應性預期(adaptive expectation)。North的總體分析框架是經濟史的。他試圖解釋世界不同地區之間發展程度的差別或績效差距。在他的諾貝爾演講(North ,1994)中,他提到經濟史中的路徑依賴與發展差距有關:由於所有國家不是平等發展的,一般來說,那些欠發達國家趕不上發達國家,因而歷史是路徑依賴的。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North,1997)中,針對後社會主義國家,他提出路徑依賴就是制度框架使各種選擇定型(shaping)並約束可能被鎖住的制度路徑的事實。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社會學教授Stark(1992)是最早把路徑依賴用於後社會主義經濟,特別是私有化戰略研究的學者之一。儘管他聲稱他的靈感來自於David 和Arthur,並接受了他們緩慢的、受約束的變遷的思想,但他仍有意無意地提出一些新的見解。他認爲,社會變遷是社會集團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私有化戰略受制度遺産的約束。他反對後社會主義的轉軌會在制度真空裏發生的觀點,強調制度變遷的進化本性。
David(1994)也是較早注意到技術上的路徑依賴和制度上的路徑依賴差別的學者之一。但他認爲路徑依賴的三個成因(技術的相關性、規模經濟和投資的准不可逆性)對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是一樣的。當制度逐漸演進並且不被看作是資源配置問題的有效解時,制度就是路徑依賴的。David的制度上的路徑依賴概念只包含了漸進的變遷,很少涉及激進的變遷,因而他的分析沒有引起制度經濟學家們的注意。
Campell(1996,1997)承認激進的變遷也可能是路徑依賴的。Hausner等人(1995)接受了制度的路徑依賴觀的核心,即制度進化受制度遺産約束,同時又聲稱這種模式不能解釋引起鎖住的機制。他們認爲制度變遷是“路徑依賴的路徑定型(path dependent path shaping)”的結果。Federowicz (1997) 批評了單純強調作爲變遷障礙的制度遺産和解釋激進變遷的有限才能的觀點,提出後社會主義的制度變遷只能用與路徑依賴相伴的所謂的“可預見的制度(anticipated institutions)”的技術作用來更好地理解。他認爲,路徑依賴對理解制度變遷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必須加上技術的或“路徑發現”的要素,即由經濟因素決定的對制度變遷的預期。
法國巴黎大學的Vincensini(2001)則接受了一個路徑依賴的包容性定義,認爲制度遺産和戰略性路徑定型行爲引起的“歷史事件”影響制度變遷的過程,制度上的路徑依賴作爲一個受制度遺産約束和可能導致鎖住的戰略行動影響的歷史累積進化過程,與技術上的路徑依賴有一定的關係,但兩者涉及制度的程度不同,有獨特的機制,並可以由路徑定型加以調和。Vincensini提出了影響和決定制度上的路徑依賴和路徑定型的三種機制,即:經濟體制、認知能力和政治因素,並把他們用於所有制結構的分析。
由Von Neumann 和 Oskar Morgenstern 於上世紀40年代發展起來、由於引進Nash均衡概念而活躍起來的博弈論在80年代經歷了一場“策略革命”,非合作博弈學說逐漸成爲經濟學的標準工具。到90年代,博弈論研究的重點已經由完全理性和共同知識轉移到進化模型,從而誕生了進化博弈論。青木昌彥是將進化博弈思想用於制度變遷研究的先驅者之一。他從進化博弈的角度,把制度看作是關於博弈如何進行的共有信念(common belief)的一個自我支援系統,這樣,制度變遷就可以理解爲參與人有關博弈如何進行的信念在臨界規模(critical mass)上發生的變化。青木昌彥(2001)認爲,系統內的變遷更可能由激發內部變遷的外部大衝擊引起,而不是連續的、逐漸的。在制度的關鍵轉折時期和隨後,主觀博弈模型的重建會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施加一定的約束,這就是路徑依賴。他所說的主觀博弈模型假定個體參與人不具有技術決定的博弈規則的完備知識,對其他參與人的策略選擇和環境狀態也做不出完備的推斷,所有的參與人都把制度看作是有關的約束,並據此採取行動。
Witt( 2000)則把制度變遷看作是習慣(convention)或協調(coordination)博弈的參與者之間策略互動的變化。這種博弈以均衡點的多樣性爲特徵,用動態的觀點看,與路徑依賴現象有密切的聯繫。在由目前已獲得的選擇機會的分佈引發的基本(underlying)博弈中,對採用某一策略的概率的偏愛(bias)使得制度變遷過程趨同於或被鎖定於博弈的一個均衡點。
歷史的路徑依賴和非路徑依賴(independence)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在路徑依賴學說不斷模型化的同時,國外不少學者還研究了進化博弈中的歷史非路徑依賴。Sandholm(1998)以簡單協調博弈爲基礎,把産生歷史非路徑依賴預測的進化博弈分爲三種模型:隨機穩定性模型、局部互動(local interaction)的隨機穩定性模型和廉價交談(cheap talk)模型。Sandholm 認爲,雖然這三種模型都體現了隨意性(randomness),但只有局部互動模型才能産生可信的歷史非路徑依賴預測。因爲一種習慣一旦建立起來,局中人就不可能通過個人努力改善其支付,也就不會有戰略性變化出現。
二、所有制和公司治理中的路徑依賴
路徑依賴理論按照由抽象到具體的邏輯,在成功地由技術變遷轉移到制度變遷的研究後,又被一些學者用於所有制和公司治理等現實問題的分析。
Jones和Mygind(1999)考察了愛沙尼亞私有化以來所有權結構的變動,結果發現,儘管存在大量的路徑依賴,重大的所有制變遷還是發生了。他們通過對愛沙尼亞進行的經濟計量學研究得出了以下幾個結論:第一,慣性在所有權分配中起著重要作用;第二,大企業和資本密集型企業更可能由外部人擁有所有權;第三,經濟績效在所有制變遷中不起決定性作用;第四,大的少數所有權股本(minority ownership stakes)提高了最初的多數所有權變化的概率,即與內部人持有的少數所有權相比,當外部人取得少數所有權地位時,他們更可能最終採取多數所有權。
Bebchuk 和 Roe(1999)把路徑依賴與公司治理聯繫起來,提出了公司所有權與公司治理中的路徑依賴理論。他們的研究發現,一個國家的所有權結構型式有著重要的路徑依賴根源,這種路徑依賴使一個國家的所有權結構型式部分地依賴於早期的型式,當這些國家早先的所有權結構由於不同的環境或歷史事件而存在差異時,即使後來經濟變得很相似,這些差別也會存續下去。
Bebchuk 和 Roe還區分了兩種不同形式的路徑依賴:一種是結構驅動的(structure-driven)路徑依賴;另一種是規則驅動的(rule-driven)路徑依賴。所謂規則是指治理公司與投資者、利益相關者和經理人員之間以及他們內部關係的所有法規,不僅包括傳統意義上的公司法,而且包括證券法和治理破産、勞工關係及機構的的相關部分,它們本身是路徑依賴的。
Bebchuk 和 Roe認爲,所有權結構的選擇在兩種現在具有相同公司規則而開始時具有不同的所有權結構的經濟中,可能是不一樣的。先前的結構影響後來的結構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效率,一個是尋租。一個公司有效的所有權結構通常是路徑依賴的。由於適應性沈澱成本(sunk adaptive costs)、網路外部性、互補性、多重最優(multiple optima),供選擇的所有權結構的相對效率部分地依賴於這家公司或同一環境中的其他公司剛開始時的結構。現有的公司所有權結構即便不再有效率,由於內部的尋租,也會具有充分的存續能力。那些享有控制權的當事人會阻止那些可能減少其控制的私人收益的變遷,即使這些變遷是有效率的。只要那些阻礙所有制結構轉型的人不負擔結構存續的全部成本,或者不獲取有效率變動的全部收益,已有的無效率的結構就會存續。
Bebchuk 和 Roe用於解釋法律規則路徑依賴的原因也有兩個:一個是效率;一個是利益集團政治。首先,即使假定法律規則只爲效率的原因而選擇,初始的所有制型式也會影響可供選擇的公司規則的相對效率。有效率的規則集依賴于一個國家現有的公司結構和制度的型式;其次,一個國家初始的公司結構型式會影響不同的利益集團在産生公司規則的過程中的權力,企業內部的地位優勢將轉化爲國家政治中的地位優勢,這種效應會強化初始的所有權結構。Bebchuk 和 Roe分析了阻礙所有權結構趨同的其他原因,如企業的性質和市場的差別,觀念、文化、意識形態和政治傾向的差別等。
Schmidt和Spindler(2000)同意Bebchuk 和 Roe對趨同論的懷疑,同時又認爲他們的分析存在不足。Schmidt和Spindler區分了兩種不同的路徑依賴:一種是基於調整成本(adjustment costs)或轉換成本作用的路徑依賴,如Roe(1997)舉的“彎路”的故事 ;另一種是從進化生物學中借用來的概念,指作爲進化近視(evolutionary myopia)結果的路徑依賴。這兩種概念對公司治理快速趨同問題有不同的含意。Schmidt和Spindler引進了互補性概念說明路徑依賴的成因,認爲由互補成分組成的公司治理體制的動態特性使得向最優公司治理體制的快速趨同不可能發生。
三、中國公司治理中的路徑依賴
上述學說對分析中國的公司治理改革是有借鑒意義的。
中國的公司治理問題是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歷史進程而産生的。這個過程大致可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79年開始,首先在四川,然後面向全國,推行了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增加企業留利改革(簡稱擴權讓利),隨後又於80年代中期推行了承包經營責任制和廠長(經理)負責制。政府通過一系列改革舉措,將企業的經營管理權逐步下放到企業行政負責人手中。因此,這一階段可看作是經營管理權的私有化階段。當時,生産資料公有制被看作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在不觸動生産資料所有制的前提下,將經營權私有化,有利於減少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成本。
第二階段,以1992年7月《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頒佈和實施爲標誌,開始進行“轉機建制” ,重點是確立國有企業的法人地位,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企業控制權逐步下放到企業,由董事會行使,國家(各級政府)作爲大股東,保留了出資人所有權——剩餘索取權和剩餘控制權。1994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開始生效。此法明確規定了我國公司的兩種基本形式: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企業法人”,股東以其出資額或所持股份爲限對公司承擔有限責任,公司以其全部資産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第三條);“公司享有由股東投資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産權,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第四條);“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財産,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第五條)。此法還規定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形式,即決策(董事會)、監督(監事會)、執行(經理人員)“三權分立”。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都要設立董事(會)和監事(會),董事由股東選舉産生,監事中必須有一定數量的職工代表,總經理由董事(會)聘任。從此,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的公司化。公司化的實質是控制權的私有化,由國家控制轉移到個人(董事)控制。第三階段,從1997年開始,中共15大重新闡述了對公有制和國有經濟主體地位的認識,明確表示國有經濟要從非關係國計民生行業和一般性競爭行業“退出”,縮小戰線,通過改制和資産重組,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和股權結構多元化。儘管文件區分了所有制和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實際上這是股權私有化的一個信號。到目前爲止,中國原有的國有中小企業絕大多數被改造成爲職工持有股權的股份合作制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部分拍賣轉讓給非公有制經濟,大型國有企業被改造成爲國有控股或參股的股份公司,少量特殊法人企業和行政性公司被改造成爲國有獨資公司(有限責任)。隨著外部投資者的進入和企業的增資擴股,國有經濟的股權逐步被稀釋。
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實際是路徑依賴的。1979年的擴大企業自主權作爲“歷史小事件”,將國有企業改革鎖定在産權改革的軌道上。儘管現在看來,下放管理許可權並不是最優的選擇,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因爲受到舊的經濟體制的束縛、人們的認知能力的局限和原有的制度的制約,當事人(改革者)只能做出這樣的選擇。在擴權讓利的過程中,由於行政管理體制尚未改革,政府職能尚未轉變,中央下放給企業的權利被既得利益集團層層瓜分了。爲避免地方政府和行業組織對企業的干預,中央決定把農村的承包經營引入企業,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推行。承包制雖然暫時解放了企業生産力,但從長遠看導致了機會主義和短期行爲。當時,許多企業實行掠奪式經營,竭澤而漁,不考慮企業發展後勁和內部經營機制的轉換。當産品供過於求、市場疲軟時,企業競爭乏力的弊端馬上顯露無遺。經過十幾年的改革開放,人們的視野開闊了,認知能力有了較大的提高,加上三年的經濟蕭條證明改革之路是不可逆的,當事人不得不借鑒國外的經驗,實行股份制,將企業控制權交給董事會,藉以明晰産權關係,使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由於原有制度結構的慣性作用和利益集團的內部衝突,國有企業改制大多採取了國有獨資和國有控股的方式,原來的經理班子和董事會成員基本重合,董事長和總經理一身二任(少數公司除外),“一把手”的權威有增無減,監督機構形同虛設,企業領導人腐敗問題頻頻出現。而且由於一、二把手(甚至三、四把手)是由上級主管部門任命的,企業經營者爲了保住官位,不得不四處活動,産生了大量的“尋租”。爲了從根本上割斷政府與企業的聯繫,減少政府直接治理的成本,國家開始實施股權私有化,一方面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和股權結構多元化,並從一些行業中戰略性退出,另一方面部分企業由經營者和管理層持股,試圖讓剩餘控制權和剩餘索取權一致,以符合“匹配”的邏輯,同時轉嫁一部分剩餘風險。股權稀釋後的國有企業並沒有有效地解決代理問題。由於目標不一致,且資訊不對稱,外部股東和國家的利益時常受到損害,資産流失、作假成風。於是,公司治理提上了官方的議事日程。1999年,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了“公司治理”的概念,提出“要明確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的職責,形成各負其責、協調